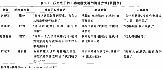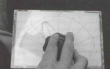,我们付出相当心力注意AHD 的活动为家庭关系、杰弗瑞与教师和朋友的关系带来的后果。我们也同时从贝丝的生理经验与安德鲁的情绪,注意到问题的结果。与莎拉对谈时(那位长期自残与忧郁的年轻女孩),我将焦点放在自我憎恨的行动对她和身体的关系,以及她与他人的连结造成何种结果。
这种针对问题的效应或影响的探索,让外化对话处于更稳固的立足点,也让普遍的内化对话有了明显的转变。例如,我开始和莎拉会面时,她告诉我,自己和其它人相比,实在很「没价值」、「没用」,还说自己「命该如此」。她也说,其它人曾试着说服她跳脱这样的结论,但对她来说,这代表他们要不是不诚恳,就是不了解她的状况。这使她开始疏远别人,甚至公开表示,会「试图做同样惊险的事」。这是我竭力避免的。然而不久后,莎拉回应我的问题——自我憎恨如何使她相信自己「没价值」、「没用」及「命该如此」。这些字词在莎拉的内在声音,及与他人的内在对话中,都是很强悍的角色。但如今在外化对话中,它们被重新表达,在莎拉的自我认同和负面结论间,开启了新的空间。当这些字词被视为莎拉的自我认同而存在时,我并未试图挑战这些负面结论。相对地,外化对话剥夺了这种结论的真实地位,提供机会让它们变得更清楚。
探索类型三:评估问题行为的效应影响
在第三阶段,治疗师支持个案评估问题的运作与活动,以及它对生活造成的主要影响。这种评估通常从以下的问题开始:对你来说这些活动是可以接受的吗?你对这种发展有什么感觉?你如何看待这种结果?对于在这里揭露的事,你采取什么立场?这种发展是正面还是负面的?或者都是、都不是,还是介于中间?对你来说这若是命运,你是否有疑问?
诸如此类的问题是邀请个案暂停,去反思某些生命中的特定发展。对很多人来说,这是很新奇的经验,因为通常都是由其它人担任评估。例如,我遇过数不清的年轻人,对自己所面临的困境后果评估是不发声的,最后是由他们的父母、教师、治疗师、社福人员、警察等人替他们发声。
对个案来说,碰到这些问题是很新奇的经验。对治疗师而言,利用第二阶段外化对话中所引出的问题主要效应很重要,做出摘要后,连同这些评估性问题做为开头。我常把这些摘要视同评论(editorals),让个案有一个平台,藉此因应评估性问题。例如,我和十六岁的维吉妮亚及她父母卢索、维洛娣谈话时,明显感受到,过去在评估某些重要事项时,她或多或少只是个过客。为了寻找她的定位,我先提出一段摘要,显示我对这些事的主要结果之理解:
麦 克:维吉妮亚,我了解你父母的心思全被以前发生在你身上的事占据,使他们特别关心某些事情。这代表他们太投入你的生活,你说这让你开始封闭自我。
维吉妮亚:对,就是这样。
麦 克:好,这对你来说像什么?
维吉妮亚:这对我来说像什么?
麦 克:对,这对你来说是什么?你的立场是什么?
维吉妮亚:我不喜欢这样。我觉得自己好像永远都被监视,我不喜欢,而且根本没有帮助,真的很让人沮丧。
麦 克:你不喜欢?你不喜欢被监视?
维吉妮亚:对,我不喜欢,而且那一点帮助也没有。只让事情更糟糕,让人非常沮丧。
麦 克:再多说一点你的感受。你还会用什么字眼来形容这种不舒服和沮丧的感觉?
维吉妮亚:嗯,那就像……
当维吉妮亚更完整地说出她的感受后,我询问卢索和维洛娣,他们如何被发生在维吉妮亚身上的事占据所有心思


 正在提交中...
正在提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