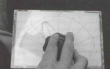那我们的想法就是你要是能够理解这样的循环系统,你就有这样的能力去控制整个系统。这样的理论怎样运用于治疗和精神科呢?那么上世纪五十年代有个非常著名的关于家庭研究的中心。那个时候我们有一部分非常优秀杰出的科学家,也包括我们一部分人类学家,以及VirginiaSatir的社工,以及Jay Hayley他当时有沟通学的学位,还有Paul Watzlavake,一个著名的哲学家,还有DonJackson也在其中,他是著名精神科医生,那么他们共同都对于我们的沟通非常感兴趣。那么他们当时的一个初衷就是去了解精神分裂症是怎么在家庭里发生的,家庭动力是怎样。他们的那种很好的想法就是不管你的过程多么复杂,只要找到他这种内在联系,就能很好的操控他。所以他们很想知道家庭怎么达到平衡的。家里的排序怎样的。在一个家庭里面,不同角色,比如妻子和母亲,怎么平衡的,以及不同代际之间的平衡,或者不同兄弟排行之中,那么当时如果说出现症状,我们就认为家庭里面平衡被打破。所以他们当时就有一些讲了这样的所谓有功能或者功能良好的家庭应该长成什么样子。这个时候他们那些基本概念,像Minuchin的想法或当时结构主义的JayHayley的想法,就认为用一个很牛的干预方式,就能把一个家庭不能良好工作的东西给改变过来。他们认为精神病学家或者家庭治疗师。可以作为一个完全不相关的观察系统,能够给他们一个诊断。那么他们美好的理想是,这些家庭治疗师在观察时并不会对家庭造成任何的影响,那个时候我们的观察者和系统是完全分开的,要不然就是做研究,或是做诊断,或是做干预,来访者就是一个表达自己不同问题的人。但随着我们时间,理论科学的进步,我们关于一个好的家庭的理念已经被批评了。
过去治疗是相信能用强有力的手段把一个家庭从一个功能不好的状态变成一个所谓的好的状态。现在我们知道家庭有多种多样的组织方式,我们说那种跨国或跨文化的家庭,还有一种组合方式,就是这个家庭离婚之后,带着自己孩子和其他带着自己孩子的重新组合的家庭。所以他们就需要面临怎样重新组织关系,重新组织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关于所有治疗师他们应该所处的角色都是被质疑的。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我们曾经说的稳态概念,已经被一个混乱或者说充满生机的系统所代替了。这个理论认为我们这样的系统是开放并且是无法被预知的。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去预测我们任何一项行动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那我们曾经有一项很著名的现象,所谓的蝴蝶效应,太平洋上的蝴蝶振一振翅膀,可能世界上另外地方会产生飓风。我们这样的理论对于我们的精神科的诊疗以及家庭治疗还有我们人类发展都是非常相关的。那如果你们想一下我们的关于康复以及教育以及其他的等等的过程。还有我们关于我们社会,组织的康复以及重建。这些发展史完全无法预测的。
我们可以去帮助或干预某些特定的发展。那么我们可以创造比较有利的环境,但是我们无法决定人类的发展。我其实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看法,因为它能让我们尊重其他的系统,并让我们充满了希望。我们的人类系统,通过这样的能力,能找到新的解决方案,并形成新的平衡,我们可以去帮助他们,但我们没有这样的能力,也没有这样的责任去控制他们怎么样达成特定的状态。这时候我要调到我们的自组织系统。你们知道的,我们家庭治疗并不只有一个流派,有非常多的流派,由此可知我们可猜想我们


 正在提交中...
正在提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