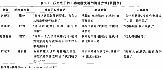斯顿)在一年前与她的小女儿卡萝,还有小儿子东尼见过三次面,重点放在东尼对姊姊们的肢体暴力。後来他的暴力很快得到收敛,在母亲的鼓励下,二十三岁的姊姊茱蒂离开了家。卡萝在整个过程中都表现得很坚强。
但是这一次事情显然与以前不同。卡萝感到非常灰心,在我们首次会面时,她告诉我:「我只告诉了你部分的真相。」现在她觉得必须要坦白。但在她合盘托出之前,她凝视我的眼睛说:「不管你要怎么做,别叫我报警!」从她的描述中,虽然东尼克制了肢体暴力,仍然会构成威胁,而且他已经因为犯法被定过罪、罚过款,在感化院待了一段时间。当卡萝不肯给他钱,或借他车子,或让他用屋子,他会暴怒,毁坏她的财物,威胁要伤害或杀死她或她的小猫。她承认她担心自己的安全。我认为她有十足的理由担心东尼正误入黑道。她觉得自己束手无策。
我把「内疚」(guilt)外化、客观化了,先是询问卡萝一连串补充性问话(White,
1986b),然後提供她的补充性描述,我称之为「我的摘要」。
「内疚会招引东尼的责怪。责怪他人能使责怪者不负任何责任。充满内疚的父母就会为不负责任的孩子担负起过多责任。」然後我给了她一些带回家思考的问话:
1. 你要如何了解自己多么容易感到内疚?你在感到内疚方面接受了什么训练?
2. 你要如何了解你们家丑不外扬的传统?为什么告诉外人就是不忠实与背叛?
卡萝一周後回来。她说这些问话都很有道理,然後提出冗长的理由,说明她为什么应该感到内疚。她从五岁开始就觉得自己要为父亲的酗酒负责,没有任何外人能知道家中的事情。在她家中「所有人都要保密」。卡萝说她对孩子们所受的苦、她自己恶劣的婚姻,还有东尼的问题都感到有责任与内疚。
这次会面结束时,我又让她把两个问话带回家思考:
1. 我为什么会觉得必须内疚?
2. 我是否已经受够苦了?还是应该继续折磨自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三周後,卡萝很紧急地打来电话,请求次日立刻会谈。她说她必须告诉我一些事情。我们次日见了面。接下来的就是在那次会面当场完成的纪录,後来也寄给了她。
你说我会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做好准备,我感到很不自在,後来两天工作都很不顺利。我回家後发现银行帐户的钱被提走了一百三十元。东尼知道我的密码。有时候我把提款卡给他使用。他曾经要我借他七十五元。第一次被提了八十元,然後是十元、二十元,第二天又提了十元,三天内提走了一百三十元。我打电话给银行关掉这个户头。我在工作上有很多压力,晚上还要上课实在太累了。
我开车回家……东尼看起来很得意,到处都是啤酒罐。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彷佛有什么东西崩溃了,我感觉好像游魂似的,又哭又叫:「我一直不停付出,付出又付出,现在我没有东西可以付出了。」我看见一个很深的大洞:「离开这里,否则我就报警!」我的恐惧消失了……一切都消失了。我甚至把他推到墙边。他还是用他的老方法:「你想要拥抱一下吗?」然後威胁要砸毁我的车子,打破我的窗户,杀死我。我感觉好极了──我再也不害怕了。「你不能对我怎么样!」我很惊讶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有一个大空洞,里面什么都没有,我甚至不怕他威胁要找人杀我。我到邻居那里要了一点酒与镇定剂,後来立刻睡著了。
第二天下班後我去看一位朋友,打电话回家问黛安(东尼的女友)的父母是否还要过来。东尼说:「是的。」我


 正在提交中...
正在提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