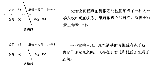黑暗中的伸向灵魂的一双手——叙事的神奇力量
二十三岁时,我爆发恐慌症,就像地狱生活一样。过了两年,我才知道这些症状和童年受到性侵害有关。直到十二年后,我才知道父亲冷酷虐待我的程度,包括性、身体和情绪上的虐待。我说不出这种侵犯对生活的哪一面造成最大的痛苦,自此折磨和混乱的感觉难陈。
终生努力和奉献的累积,使我达到表演艺术生涯的巅峰。我在专业生活上,缓慢艰难地向上攀爬,却在内心映照出软弱的感觉,好像被吸入虐待的消极深渊。我当上一家著名制片公司创作部资深副总裁,在这同时,我正接受第十二位治疗师的治疗。不断拒绝各个治疗师愈益急迫的住院和服更多药物的要求,我觉得身心俱疲,难以承受。加上财务重担即将崩溃,我为一生梦想所努力的每一件事,好似即将全部丧失。我的情绪瘫痪,力不从心,终致大约七年前,一份长达三页吹毛求疵的心理评估,使我产生自杀的念头,膨胀到我无法处理的程度,以致我看不到任何正面的事物。
受伤害的过程布满混淆和挫折,又笼罩着神秘的气氛,使我觉得再度受到伤害。我无助地坐在过去虐待的黑暗中,听凭一堆“专家”评断我的“错”,我充满了痛苦,那真是段混乱的时期。
我觉得不可能得到什么远景,于是退缩到朋友家中,她无怨无悔地为我的需要提供支持。我第一天“封闭情绪”时,接到另一个朋友舒曼的电话,她常常热烈谈到治疗师的工作。听到她对个案真实觉得同情的程度,还有对叙事团体中同仁和良师的尊敬,我有时会觉得充满惊奇。她温柔地恳求我考虑与吉尔的门诊,她说:“这次会不一样的”。我做了,结果真的不同,治疗的冲击产生明显的转折点。
吉尔为我治疗的过程,剥去可怕黑暗的硬壳,一度让我觉得受吸引、充满挑战、得到启发,一点也不觉得神秘或受到威胁。我觉得自己以前好像坐在充满荆棘尖刺的道路,受到包围,没有什么选择可言。吉尔现在却站在我的旁边,劈开荆棘,让我看见自己想选择哪一条道路。她让我看到各种选择的可能,所以我有机会自己选择。她和我核对时好像在说:“有什么地方是我们可以去的呢?”如果我卡住的话,她可能说:“你认为我们可以去这里……或是哪里?”我也觉得可以自在的说是或不是。我在治疗旅程中,有时可能坐着述说故事,或是在觉得疲倦时,只是静静坐着。每一步她都陪着我,而且了解我,这一直令我觉得惊奇而感激。
我开始走上愈合的过程。
我现在试图看清如何把虐待与我分开,一点也没错,这是种摘取,我把虐待的阴影从我身上拉出。
在朝向愈合的每一小步中,我常常发现自己对这是一件“好事”会起激动的反应,因为在痛苦醒悟童年虐待时,觉得没有一件事可以看成“好的”。所以我们把道路分成“白色的方向”,表示能对抗虐待,和“黑色的方向”,表示会强化虐待。我缓慢而谨慎地体认到,如果我想超越这个恶毒的障碍,就要承诺走向白色的方向。“白色的工具”则成为这个方向的象征,对我而言,包括音乐、蜡笔、蜡烛、接受爱与支持的意愿(不管多难受)。我逐渐把“黑色的工具”交给我的朋友舒曼,我欠她太多了,理由很明显,却很难用人间的语言说明。
我最惊讶的,是发现治疗真的有效。我要以一点感伤和轻浮的玩笑对你说:“过去那些人为什么不知道呢?”
接受叙事治疗,种下我承诺“白色方向”的种子,而我也一直受到团队同仁恒久的耐心、了解和得体同情的培育,这些是我以前不敢相信会有的。
我希望这种疗法能吸引许多人看见“白色的方向”,并对有人关心、有人会努力在璞石中见到钻石抱持希望。在问题和痛苦的毒性下,隐藏着闪亮的独特性,终将浮现其意义,并对我们的存在发出惊人的贡献。我们能依此清除荆棘,看见路上有着许多可能性。
摘自《叙事治疗——解构并重写生命的故事》


 正在提交中...
正在提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