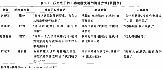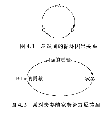杖。 索德家人出现在第八回诊疗时,大维没出现。理查看不出他来的必要。米纽庆决定不要节外生枝。虽然在一般情况下,没有获得家庭关爱的兄弟姐妹,另有自己的问题,但时间有限,而且还有更严重的病症要处理。 全家人一起进来,米纽庆很高兴看到理查带着一把看起来相当坚牢的新雨伞。不像一般治病师。他们只专注个人,而且必须仰赖病人报告生活发生了什么事件。家庭治疗师可以把他们的生活搬到治疗室。在这一回合里,米纽庆将强化第一步,藉教吉尔用拐杖走路,让理查更亲近女儿。 理查试着帮女儿站起来,递给她雨伞,问她是否能拄着拐杖支撑自己。他还不习惯扮演护士角色,吉尔向母亲投去哀求的一瞥。 “很好,”米纽庆说,“珍妮特和我会站在房间的另一边,让你们有更多空间进行练习。” 现在理查果断了点,成功地让吉尔拄着雨伞单独站着。在他的有力敦促下,吉尔走了几小步,然后啜泣,塌倒向椅子。“我害怕!”她的父母看起来很烦恼。吉尔很可怜,很无助。 对他们三人来说,这是个困难时刻。要母亲退到后面只当观察者,实在很难。吉尔怕跌倒,过多的关注她那无法使用的腿,她的麻痹来自真实的恐惧,父亲急着想帮她,但不知该如何着手。忧虑和挫折让他有点苛求。女儿的眼泪软化了他,但是他挫败的感觉更甚于同情。 “做得很好!理查,你必须帮助女儿克服恐惧,非常好。你们俩开始的很棒。” 对索德一家来说,现在的课题是吉尔要学习走路,即使他们都很怕。对米纽庆来说,他的课题是延长父亲与女儿的互动,并帮助父亲,让他觉得自己有能力,他对女儿的帮助很成功。 大多数父母是不常跟子女玩的,但米纽庆会被父母带来治疗的所谓问题儿童一起玩耍。 “吉尔,你的困难很不容易让别人明白,所以让你的父亲了解,教他象你一样走路。” “我要你观察,理查。你有没有观察她是如何变换重心的?” 米纽庆请他卷起裤脚,让吉尔看看他脚的移动是否恰当。卷到小腿时,他不好意思轻声说:“这样行吗?” “不行,不行,”米纽庆说,“再卷高一点,我们要看你的肌肉是如何动的。” 理查很合作,他象玩游戏一样,把裤腿卷上大腿,在房间里跛着走来走去。珍妮特想保持严肃脸色,但实在忍不住,爆笑起来。吉尔望着父亲踩高跷似的难看走路样,也笑开了。理查很尴尬,但没多久,尴尬就消失了。他朝米纽庆扑了过去。 米纽庆也乐在其中,他觉得自己象电影导演,指导演员做怪动作,并且准备拖长这一幕。 于是米纽庆告诉吉尔,她父亲的动作学得不够正确。她可否抓住父亲的手臂,现身说法。因为吉尔对跛行是行家。 米纽庆告诉他:“这特别需要心灵的力量。你看,她的心灵告诉她‘弯曲走路’。她真的弯弯曲曲走路。因此,你的心灵也能这样告诉你。理查,我要你对自己的心灵说‘弯曲走路’,就象吉尔的心灵对她说的一样,然后你们一起走,看看是不是走得弯弯曲曲。”“弯曲(Crookedly)”,米纽庆开始玩这个字,“r”这个字母,他用了西班牙的卷舌音,并读出节奏,还打着拍子。他们俩跛着,在房间穿梭,这对奇形怪状的父女,进行着仪式性的舞蹈。 “你必须要有弯曲的心灵才能学得好,理查,你们的心灵还没有进入状况,还是太‘直’。”这一次,大家都笑了。在严肃的暗示下,他们全部参与了这荒缪的一幕。 就象任何一个症状一样,麻痹症在家庭的心灵结构上,也带有许多目的。因此,对这一症状做简单挑战是不会成功的。


 正在提交中...
正在提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