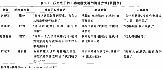位置上,像块怨恨的石头。 接着珍妮特说:“我知道双方互相怨恨。” “太强烈的字眼,”她母亲说道,希望事情缓和下来,“只是偶尔有些不满。” “你不满意什么?”珍妮特想知道。 “他对你的行为,以及对大家的行为。” “你先提到他对我的行为,你指什么?你曾经这样对理查说过吗?” “等一下,”米纽特说,“珍妮特,你必须帮助母亲,方法之一就是让她知道理查对你的行为不关她的事,如果你能帮助她,她就会跳出你们的婚姻关系。你办得到吗?” “我没有跟她讲过太多什么。”帕斯奎瑞罗太太说,没有人乐意染上爱管闲事之嫌。 “哦,妈妈。”珍妮特说。 “你的事我看到的不多。我只看到你的负担。” “妈,我不觉得那是负担,那只是家务琐事。如果我觉得有负担,会找你讨论的。” “珍妮特,”米纽庆说,“你觉得你母亲怎么看你?”她笑着说:“比吉尔还小。” “所以你让她保护你?” “唉,她是很难抗拒的女士。” “不过,虽然她喜欢管闲事,但这是得到你认可的。要想帮助吉尔,方法之一就是建立可接受的界线。如果你帮助母亲,不让她介入你的婚姻,就会建立模式,不让女儿介入你的婚姻,因为她也很会管闲事。你的母亲管闲事,但有帮助。你的女儿管闲事,却是过分要求。” 吉尔没有病,她是在介入和管闲事。她在扮演外祖母的角色。这真是恐怖的传统。 理查开始说话了:“我想问一个问题。你父亲表示了一些意见,我想知道,你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感觉?” 米纽庆赶忙打断:“在你回答之前,我要你了解理查话中含义。他是在问:‘你站在我这边,还是站在父亲这边?’” 再度的沉默,接着珍妮特说:“我站在你这边。”她似乎是真心的。 几分钟后,珍妮特的母亲在谈话中又插嘴提问题。 珍妮特说:“妈,拜托,我们正在私人交谈。” 很容易就可看出外祖母的介入与多管闲事造成了问题。但是,界限不清却是由双方面造成的。当某人介入,另一方就必须忍受。米纽庆很高兴珍妮特采用他的语言,来建立界线与独立自主。 吉尔是问题,但不是唯一的。另一个问题是吉尔的祖父母认为珍妮特与理查之间未解决的冲突需要他们的帮助。 十天之前,这家庭的情况可清楚界定为:他们是正常家庭,有位出现病症的小孩。结果导致大家努力照顾小孩,放大了帮助,却窄化了选择性。现在这个定论出现了新的挑战:情况并没有那么清楚,困惑可能激发出新的观点。 治疗的推进有好几个层次。虽然米纽庆强调与整个大家庭的问题,吉尔的症状并没有离开他的关注,或整个家庭的关注。自从把父亲当作拐杖,吉尔已经更有活力了,但现在是走得更远的时候了。 诊疗接近尾声时,米纽庆问吉尔自从意外后生活有什么混乱。她提到行动不方便与看了很多医生,对于跛脚似乎没有特别难过。米纽庆告诉她与她父母,进一步的康复计划是吉尔必须学习在没有父母的协助下走路。他将请教儿童医院的整形外科,然后造出吉尔专用的特殊拐杖。在这同时,米纽庆也告诉理查,在下次诊疗时带把坚固的雨伞,他可以开始教吉尔走路了。 用心灵走路 下一回合之前,米纽庆接到神经科检验报告,在研究过病历,执行所有必要的检测后,神经科医师找不出任何器官或结构上的理由,说明为何吉尔无法正常行走。报告上说:“所有功能都能完全正常运作。”吉尔的疾病在她心里。 吉尔被送到整形外科,做出适用的拐杖。技术人员问吉尔,有没有喜欢的颜色,是紫色。她有了一根紫色拐


 正在提交中...
正在提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