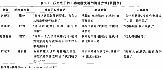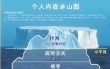离,当人们不再受限于自我认同是唯一的「事实」,不再受限于对生命的负面认定,对生活困境采取新行动的选择变成可能。这种将自我认同与问题分离的做法,并不会让人放弃自己面对问题的责任;相对地,它让人们更愿意承担起这份责任。如果问题等于人,除了自我毁灭外,几乎别无他法。但假设人与问题的关系能被界定得更清楚,如同外化对话的技巧,许多修正这种关系的可能性就会随之出现。
摆脱负面认同的结论
外化对话也使个案得以摆脱受问题影响而得到的自我认同负面结论。曾有位年轻女子莎拉找我咨询,她有忧郁与自残经验,强烈地相信自己是「可恨的」,并因此憎恨自己,在她的感受中,「自我憎恶」是主要经验。我们很快投入讨论,想探索自我憎恶的情绪如何说服莎拉相信自己的自我认同——「我是个没用、没价值的人,一切都是我活该」;如何让她伤害自己的身体——「抵制、惩罚我的身体」,以及如何主导她与别人的关系——「让我变得孤立」等。
这开启了进一步将自我憎恨具象化的可能性。我试着厘清这个自我憎恨的所为,如何反映出它对莎拉的生活所抱持的态度,以及如果它是真正存在于世上的声音,它会说哪些话。如此将自我憎恨拟人化,提供了探索的基础,追溯出这些存在于莎拉经验中的态度和声音所造成的回响。这让莎拉首次得以将自我憎恨与她童年时的施暴者的态度和声音连结起来。外化对话促使这些关于憎恨的结论得以被摆脱,也开辟了发展重写对话,(re-authoring)的空间(见第二章)。随着这种对话的发展,先前持续在莎拉生活中出现的自残与忧郁都急速减少。
这种解放过程,普遍显示出让个案前来咨询的「问题」长久以来采用哪种「策略」。这些故事包含种种人们所臣服的权力关系,以及在他们的生活与自我认同中形成的负面结论。这种解放使「事实」失去地位,种种负面结论被画上问号。结果个案发现生活不再受制于这些负面结论,并演变为能够探索生命领域的状态。在探索中,他们一定会对自己的自我认同得到更正向的结论。我发现外化对话非常有用之处,在于它解放或解构了人们对生命的负面结论。


 正在提交中...
正在提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