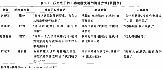患者受到鼓励去探索各种各样的叙事方式,而不必承认某种方式是真的。叙事不但是帮助患者和治疗师理解意义的一种方法,也是创造意义的一种方法,意义是语境的一部分,而语境没有终极或真理。通过叙事经验,他们将会认识到一种叙事并不比另一种叙事更好或更重要(Grgen.1994b) 。在安德森和吉尔利希安(Anderson & Goolishian.1992) 看来,叙事通过在新的语境中表达生活意义的方式,获得了它的转换力量。治疗师对患者表明,治疗师不会有任何的假设、答案或期望——就是不了解但的确有着巨大的好奇心,想听到更多信息。治疗师不可避免的要去帮助那些渴望改变的患者克服问题,但是他们能改变作为专家的治疗师的社会期望(Fruggeri.1992) 。治疗师不能避免他们的知识和偏见或他们所接受的参照信息,但他们能避免采用不了解的观点去扼杀新意义。正如安德森和古尔利希安(1992)所描述的治疗,在不了解的过程中,治疗师避免提出问题或疑问,并试图鼓励患者使治疗师获得新的理解。不了解的问题会在双方之间重复叙述和展开的故事中得到局部建构的词汇和理解。这为情感、历史和知觉提供了一个连贯的叙述。安德森和古尔利希安认为,这种方法促进了在一种治疗中被认为是成功的解脱感。
这种治疗形式的一个例子是,一个41岁的男性确信自己患有传染病,并已经威胁到了其他人。医疗检查后,排除了他患有任何传染病的可能性,但是他仍坚信不已。他求助于精神病医生治疗,但没有获益多少。一位精神病医生最后向古尔利希安提到了他,古尔利希安没有过多询问这个男人的故事,但他对此表现出了兴趣。这似乎让他轻松不少。通过询问"你患这种病多久了?"等此类问题,治疗师鼓励他复述这个故事,从而揭示新的意义。这种"不了解"的方法看起来获得了有用的结果。当这个男人回访他的精神病医生时,医生报告他的生活比以前有了进步,他正在处理职业和婚姻问题,而不是传染病问题。这种"不了解"的方法开辟了治疗过程的新局面。
某些方法
建构主义使用的治疗方法包括:讨论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讨论问题(de Shazer, 1993) ,帮助患者写信和创作其他作品,以重构他们的生活(White & Epstein, 1990) 。通过各种各样的谈话手段在治疗师和患者之间达成协议(O'Hanlon & Wilk, 1987),关注患者自身的积极特征( Friedman & Fanger, 1991;Durrant & Kowalski, 1993) ,通过使用木偶来叙述他们的状况,研究残疾青少年(Coelho de Amorim &. Gavalcante, 1992) 。
家庭治疗
种类繁多的家庭治疗在建构主义的临床实践中已经变得非常重要。它将行为看成是循环因果关系的家庭系统的一部分,家庭系统涉及家庭成员之间循环的因果关系,而不是作用于个体的过去事件的线性因果关系。女性主义运动、社会建构主义和文化相对论在重塑家庭治疗中都具有很重要的作用(Hardy,1993) 。女性主义使我们关注这样的事实,即我们生活在父权制社会中,男性施发号令,女性服从;文化相对论坚持,生活的所有方面都受到文化的影响,因此治疗不能忽视文化。什么是正常机能的,什么是机能失调的,会随着文化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正如美国黑人的传统根植于非洲价值观念,认为团体的联合超过个人的权利。
家庭自身是一种类型单元,其中治疗师和患者,都是成员。由于治疗师与患者具有共同的经验,所以治疗师参与建构个人的家庭问题,其中一些也许正是患者所面临的问题。在个人建构主义治疗中,治疗师不再是一个权威或专家,而是


 正在提交中...
正在提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