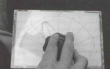主义者的道德责任是让人们的生活不受专家们掌控,并且:
将他们生命中各种形式的责任,交还到彼此产生关系的人手中——此任务目前即是认清那些人们可能会以道德生物身份而彼此冲突的时候与情境。(引述舒特,1995,p.387)
其他人也提出同样挑战。心理学家马克.富利曼(MarkFreeman,1995)主张,“自由与责任的议题只对少数心理学家是明显的,一般而言,学术领域的假定不容许这种情况发生”(p.357)。他区分道德责任,视之为“为自己行动负责”(p.358),以及“对他人的责任,尤其是对那些权利受损或遭受不必要痛苦的人”(p.358)。有些认为自我是关系取向的女性主义哲学家、心理学家和妇女研究理论学家(Code,1998;M.Gergen,1995;Hughes,1988)也强调责任的观念:玛丽.葛根(1995)提出警告:“这种朝向关系取向自我的行动,并不能根除道德选择与行动的语言……但是认为需要修正那些透过多元论的滤镜而构成道德行动的事物”(p.366);罗芮妮.寇德(1988)要求负责任的知识;茱蒂.乔丹(JudithJordan,1991)主张责任的共同性。
肯尼斯.葛根与沟通研究学者席拉.麦克纳米(SheilaMcNamee,1994),认为探索关系取向责任的目的,既非改变有缺点的人,也不是解决冲突,而是去扩展相关声音(关系取向的现实)的范围。更负责、可信是让治疗师能更开放、公开与更具弹性的原因之一。
“但是你才是专家”
治疗师往往担心案主会期待确定性,他们付钱给专家寻求答案,却不接受采取哲学立场和鼓励合作的治疗师。依我个人经验,并不需担心这点,我发现要求案主加入这种合作文化并不困难。正如舒特提出的“归属感”,案主内心接纳需要这种文化。如同那位两个女儿患厌食症的瑞典母亲顽强地认为,案主通常要求这种合作文化:“但我们比任何人都了解自己的女儿,了解她们的感应和感受……我们比任何护士或医生更了解何时能信任她们。”
不幸的是,当治疗师碰到像是这种家庭成员自认专家比本身更了解自己和彼此,以及何时专家的了解会产生令人可疑的叙述与遭到轻蔑的对待。然后,专业人员参与创造他们所见的事物。例如,若一个人是以怀疑的方式被倾听或对待,那么很可能其往后的所有行为都会被人用这种方式看待,他或她可能真的开始表现出证明可疑的行为方式。例如,一个相信父亲骚扰女儿并想证实此事,想要跟这位父亲进行对话的治疗师,对待他的方式可能会有相当大的差异。
怀疑案主以合作方式参与的意愿与能力,主要是跟我们自己的期望、我们对于不确定性的不安有关,而跟案主的关系很少。这并不表示我漠视案主的要求:“告诉我,该怎么办。”当然,有些案主会这么做。发生这种情况时,我尊重他们的意愿且认真看待他们。然而,我并不假定自己知道他们想要什么;但我也不忽视他们的要求,期待他们盲目的信任我。我响应他们的每一项要求,且每次响应都取决于当时那个要求的谈话背景。
刻意
请记住,哲学立场是展现其自身概括一切存在方式的一部分,并且是从案主—治疗师接触的第一刻起,案主所体验的事物。合作的舞台在刚开始接触中就已建立,且在从头到尾的关系中都要被照顾到。这个立场不是某种技巧或理论,不像以认知方式思考所暗示的具有操弄性、策略性,也不是计划性的。它不是刻意呈现出来,不过,它是有意图的。我刻意想要开放、真诚、重视、


 正在提交中...
正在提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