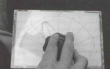,且使得意义的建构发生在普遍性的领域而非局部的领域中。例如,它就会把某个儿子对同学开枪的黑人单亲妈妈排除在外。当治疗师采取叙事的编辑立场,就没有讨论这位母亲的空间,因为她并不属于此领域,这不是她的故事。接着,这位母亲的假设和恐惧,自认为她的处境无法被理解或得到协助也会获得证实。更重要的是,叙事的编辑扮演掌控的角色,治疗师在其中处于相对于案主而言是有阶级之分且二元性的立场。这其中存在的危险是:将这位母亲第一人称故事边缘化且偏向主流社会论述。即使是自称跟主流社会论述奋战的治疗师,当他们假设其反叙事(counternarrative,例如,社会不公义、性别不平等、制度性的殖民化),对于案主较有利时,也会不经意且吊诡地将案主边缘化。
治疗师不是一张白板或空白屏幕。犹如那些跟我们谈话的人一样,我们也是带着自己的知识、过去的经验和各种成见,即我们的预设立场(Gadamer,1975,1988,Heidegger,1962)而进入治疗领域中。我们应尝试不带偏见地抱持它们。例如,对于案主应如何接近问题的解答,我们不要有预设的计划,而应该相信通过谈话的发展能够达此目的。
治疗师不是协商者或异议的裁判员。治疗师也不应企图面质或指出差异性。治疗的目的不是要努力寻求融合或共识。治疗师反而要鼓励不同的意见出现。
治疗师并不是发现真相或是非对错的侦探。治疗师并不寻找隐藏的真实、意图和意义。治疗师并非单方面和掌控全局的调查者,也不是界定问题的专家和问题解决者,或判别病状和正常的权威。治疗师不是行为的描述者、解释者或诠释者,是对话的伙伴。
治疗师不是介入者,治疗师也不是消极的。我想要强调,它不是一种机械性的、干涉主义式的预知方式。受到案主引导的治疗师,就如同伽达默尔所认为的,他只是“循环的互动系统中的一部分”(Gadamer,1975,p.361),只是互相影响系统的一部分,而非该系统的掌舵者。例如,治疗师并不借由设定好的计划,或朝着某个特定方向的内容或结果的发展来控制说话,治疗师也不为方向的转变负责。治疗的目标不是主导或介入,而是协助对话的顺利进展,而通过对话创造出最大机会,使得意义、叙事、行为、感情与情绪各方面都产生新意。治疗师旨在鼓励内在对话(与自己或想象的他者之间静默无声的自我谈话),以及外在对话(与他人进行说出来的谈话),而非介入;不去划分阶级式的立场,并不等同于消极或无知。它并不代表任何方法皆行得通而随意发展,即治疗师失控或不具影响力。在此立场中,治疗师的态度虽积极却不发号施令。治疗师永远在影响案主;同理,案主也永远在影响治疗师。
治疗是在治疗关系的“存在”(being)VS“做”治疗(doing)
依此观点,治疗也把发展和治疗师个人的风格运用考虑在内。每个治疗师都会把这种治疗哲学和相关的立场,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于治疗关系中,这个方式对治疗师的为人风格和每个治疗师具备的所有特质而言,都是自然且独特的。每个治疗师对治疗哲学和治疗立场的解读都是高度个人化的,且在每个治疗情境的展现都是独特的,包括参与其中的个人、谈话的相关性,以及谈话的脉络。换言之,治疗师的谈话和行为会随着每个案主与每次治疗的不同而有差异;它对于治疗师与治疗情境都是别具特色的。这种“随情况需要而采取行动”(donging—what—the—occasion—calls—for)需要应变性。它


 正在提交中...
正在提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