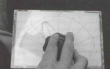n,1993,p.350)
公开化并非局限于专业信息,而是包括个人的信息。在此所谈的并非所谓的自我暴露,或因分享个人秘密或在亲密性意义下产生侵犯界限的情况。尽管我并不反对也不像某些治疗师那样,迟疑让他人知道关于我的事。案主很自然会对我们感到好奇:这有什么不对呢?还记得莎宾娜说过的“我对你一无所知”,以及后来又说她在猜测(指其治疗师):“她结婚了吗?她的婚姻关系如何?”最后,在治疗结束时,她又提出疑问。
另一位案主晤谈时提及她跟三位治疗师相处的经验:“你原本信任自己的治疗师,实际上却对他们一无所知,这岂不好笑?这好比你总是赤裸地站在一个永远衣着整齐的人面前。能够多了解别人总是好事。”
因而,每次治疗结束时,我总给案主和在场的每个人机会问我问题。在某个典型案例中,我告诉一位案主:“我已经问了你许多问题,所以我心想你是否也有任何问题想问我?”
“我对你在德州所从事的工作有些好奇。”他回答。
我告诉他一些有关我的工作,我有兴趣多了解像他这样的人,还有他们所面对的各种困难,我以“可以吗?”做结语。
他说:“这非常有趣。”
“你还想要知道任何事情吗?”我问。
他只是回答:“我想这样够了。我把这个当成是更了解自己和周遭情况的机会。”
为了让一个人对于案主的要求能抱持更开放和反思的态度,以尚恩的话来说就是:“专业的实务工作者为了扩展和深化其在行动中反思的能力,应该发现和重构被带进其专业生活中的人际行动理论”(p.353)。我还要加上,“以及被带进其个人生活中”。有些理论并不容许对这类本质进行反思;它会是一种内在的矛盾。例如,开放、公开性的反思可能被视为不具实证性研究所谓的信度和效度,甚至可能被视为侵犯保密原则,是越界、未保持中立或可能被视为过于相对主义。更重要的是,它们可能威胁到知(knowing)和专业知识本身的坚固与确定性,进而威胁到理论本身的存在。
共享的责任与义务
责任与义务是文化的理念和价值。我们希望人们能负责任并且对自己和他人也有责任感。然而,有时我们并未创造脉络和关系去容许或鼓励它发生。相反的,我们创造各种不必负责任的情况。我们被训练成参与不平等的谈话,被训练取走案主身上的责任。例如,我们被训练成了解人们该如何过生活,什么是一个好的叙事,或什么改变是最有效用的专家。
依我的经验,当一个治疗师鼓励并容许案主合作时,彼此便开始分享责任。人们往往把运用合作取向的治疗师,误认为单纯地放弃治疗师的责任,但情况并非如此。当治疗师采取这种反思式哲学立场,在案主与治疗师之间的二元性与阶级性就消失了,彼此开始分享责任与义务。事实上,我发现在共享的责任与义务中,治疗师对案主甚至会变得更尽责。
有些社会建构主义者面临道德责任的议题。舒特(1974,1975,1990,1995a)主张并要求增强与分享责任和义务。他希望能“重新建构心理学成为一种行动的道德科学,而非一种行为(和机械论)的自然科学”(1995a,p.385)。舒特(1995a)的底线是,“要求承认一个人自身独特、特别的”内在经验”(我们自认为知道),一般来说在世界无法产生影响,除非一个人能够以某种对他人负责的方式提出它们”(p.386)。同样的,分析哲学家麦金太尔(AlasdairMacIntyre)指出,社会建构


 正在提交中...
正在提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