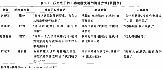我们都偶尔受困于双向束缚,但精神病患者却要经常应对它———结果就是变疯。不能对这样的困境作出反应,精神病患者常常采取防御,或者仅仅直接、表面地给出隐晦的回答或者比喻。最后,精神病患者就像妄想症患者那样,会认为每一句话都有隐藏的涵义。
发现精神病患症状在某些家庭中有意义可能是个科学的进步,但同时又带有道德和政治的暗示。这些观察者不仅将自己视为杀死家庭怪兽解救“目标病人”的骑士,也将自己视为圣战中的战士来反抗精神病学的基础。面对众多敌对的批评,家庭治疗的拥护者挑战着认为精神病是生理疾病的传统假定,各地的心理治疗师们群起欢呼。不幸的是,他们错了。
对精神病患的行为观察似乎适合一些家庭,但并不意味着家庭造成了精神病。从逻辑的角度来说,这种推论过于轻率。令人悲伤的是,有精神病患成员的家庭长期以来苦于这一假定,他们还要为孩子的心理疾病灾难而受到责备。
在有关双向束缚的论文发表之后,很多项目开始一起访谈父母和他们的精神病患子女。这些会谈的探索性多于治疗性,但是确实代表了一个主要的发展:实际去观察家庭的互动而不是只去猜测。这些联合家庭会谈促进了家庭治疗运动的开始,我们将在下一个部分讨论它们揭示了什么。
Bateson团体的所有发现都结合在一个点上:家庭作为一个组织的沟通中心。他们总结认为,是病态的沟通使得家庭呈现病态。他们所不同意的是所观察到的模糊行为的潜在动机。Haley相信偷偷摸摸地争夺人际控制是造成双向束缚的推动力;Bateson和Weakland认为最急迫的是要揭示不能接受的感受。但是他们都认为即使不健康的行为也可能适应于家庭环境。这个天才团队的两个最重大的发现分别是:(1)沟通的多种层次;(2)关系的破坏性模式可以保存在家庭互动的自我调节之中。■
帕洛阿尔托心理研究所The Ment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Palo Altohttp://www.mri.org/


 正在提交中...
正在提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