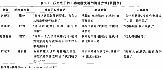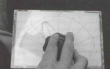有一种很奇怪的病情转移(shifting disturbance)的现象,那就是病人常常在医院有所好转,但是一回家病情就会恶化。有这样一个俄狄浦斯再世的奇怪个案,Salvador Minuchin治疗一个住院的年轻人,他因为试图抓瞎自己的眼睛而多次入院。这个年轻人在医院表现正常,可是每次回家就会有自残行为。似乎他只能在精神失常的世界,才能变得精神正常。
后来得知这个年轻人和母亲非常亲密,在父亲神秘消失的七年中,他们的关系变得越加紧密。父亲是个病态赌徒,他在被宣布失去法律的行为能力之后很快就消失了。有谣言说他曾被黑手党绑架。当父亲非常神秘地归来时,儿子却开始有了奇怪的自残行为。或许他是想将自己弄瞎,这样他就不能看到自己对母亲的迷恋和对父亲的憎恨。

但是这个家庭不在古代,也不在希腊,SalvadorMinuchin也比诗人要更加实用主义。所以,他首先通过和他妻子直接对话,挑战父亲去保护儿子,接着挑战父亲蓄意贬低妻子的态度,这使得她觉得更需要儿子的亲近和保护。治疗对于家庭的结构是个挑战,当时精神科的同事认为,将这样的年轻人送回家庭是很危险的做法。
Salvador Minuchin质问父亲,“作为父亲,儿子在危险中,你所做的是不够的。”
“那我该做什么?”父亲问道。
“我不知道,”Minuchin回答说,“问你的儿子。”接着,若干年来第一次,父亲和儿子开始对话。正当他们没什么话好说时,Minuchin对这对父母作出这样的评论:“用一种很奇怪的方式,他在告诉你们他愿意被看成是一个孩子,当在医院的时候,他23岁;可是一回到家,他就变成了6岁。”
这一个案最戏剧性的地方在于彰显了父母有时候怎样运用他们的孩子———作为缓冲器去保护他们自己不能处理的亲密关系———孩子又是怎样接受了这个角色。
对于那个可能成为俄狄浦斯的年轻人,Minuchin说,“你为了母亲要抓伤自己的眼睛,于是她就可以有些事情可以担心。你是个好孩子,好到要为父母牺牲自己的孩子。”
这些个案以及其他类似的个案说明家庭是由非常奇怪的联合组成,他们互相伤害但却不轻易放手。很少有人用彻底的恶意来攻击家庭,虽然这些观察背后存在着令人厌恶的潜流。家庭治疗的官方故事是尊敬家庭体系的,但或许我们没有人能忘却青春期的那个想法:家庭是自由的敌人。
病人的改善对家庭的影响也不总是负面的。Fisher和Mendell(1958)报告了大量病人的改变对于其他成员的积极影响。然而,无论对病人或对家庭的影响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都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改变了一个人,就改变了一个系统。小团体动


 正在提交中...
正在提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