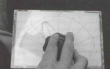一个步骤:我们怎么样把症状变到关系的层次,让我们能够去探索这个家庭,帮助这个家庭看到我们所看到的不同的可能性,然后得出解决这个问题不同的方法和策略。
李维榕:当家庭看到这个问题并不属于一个个人,而是跟大家都有关系,怎么样维持关系,也是很重要的关键。这样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本质就有很不一样的理解,当你的理解不一样,你的处理方法也就不一样。在最后的阶段就是有新的可能性出来。
Minuchin:很同意这个说法。我觉得这个治疗是一个搅扰家庭系统的历程。很多人说我们的生活是未经检验的,这样的说法,李老师说将来会影响我们的大脑,影响我们看事情的方式。
李维榕:大脑的研究也表明,其实我们很多思考和活动都是没有经过思考的,自然的反射。
Minuchin:治疗师就是要去阻止,或者去打断这种自动化的互动模式、自然反射。所以家庭要让自己的角色有更多的弹性,不要那么确定事情应该怎么样,还有更多不确定性的存在。说治疗师就是无知的专家,是矛盾的说法,虽然矛盾,但又是双向都成立的说法。我虽然对你们家庭的问题是无知的,但是在人际互动关系上,我是一个专家。
李维榕:接下来我们要谈谈些什么呢,我们来谈谈中国。
现在我们来谈谈在中国的治疗经验,Minuchin医生曾经到过中国三到四次,我们见了一个家庭,有一个八岁的小男孩,参与的人有父亲,祖母,以及一些亲戚在场,大概进行了两次的会谈。这个小孩在第一次的时候不断地大叫、不断地打人,甚至说要打老师,当时说的老师指的是我们。她打了祖母,祖母阻止了他,他就不断地跑掉,离开这个房间,我不断地请父母把小孩叫回来,重复了很多次,最后才可以成功地带回来,也许是因为太累了,不再闹了。
那个小男孩的表现,是想在父母和祖辈当中展现他的重要性,我会探索父母和祖母之间的关系,然后我想引导父母去承担指导和教育孩子的责任。有一个假设:母亲和祖母的关系之间可能存在一些问题。
李维榕:现在是否回想过当时是怎么做的?
Minuchin:当时并没有给父母和祖母解释这么多理论,只是给她们一个任务,请她们去体验会谈的例子,体验其中的技术,从这个经验中学习。
李维榕:他们从不成功,到慢慢地变地成功起来。
Minuchin:这样的方式其实是跟我自己刚开始有关系,我必须要去尊重、观察这个文化,保持对这里文化和语言的怀疑态度。用这样的精神我告诉父母:必须要承担管教你孩子的责任,必须要去操作,通过这个操作的过程去使用你身为父母的权利,怎么样去管教你的孩子、怎么样支持你的孩子、怎么样爱你的孩子。同时我并没有挑战祖母的权威,只是让她能够了解到父母有这样的权利是多么地重要。
第二个会谈的时候,我工作的重点放在夫妻的次系统里面,我的目标越来越清楚,对我来讲在那个时候,我会想让这个先生知道,你不止要尊重你的妈妈,还要支持你的配偶。在你结婚的时候就必须要去爱她,我看到他们的核心家庭和原生家庭之间是没有界限的,当没有界限的时候,他们互相干扰,互相渗透。我让父母理解到,这是他们的责任,而祖母的是可以去帮忙、参与,但主要的责任还是在父母的身上,所以说应该让他们各司其职,各有所为。
我们刚才谈到这个问题的症状并不是在一个层次,而是在更大的系统上。怎么样把观念传递给家庭是很难的事情,是一个挑战;怎么告诉他们说:问题不在你们孩子的身上,而在你们


 正在提交中...
正在提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