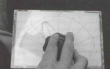怀特的合作者戴维.爱普斯顿(David Epston)出生于加拿大,他最初学的是人类学,后来移居新西兰。与怀特一样,爱普斯顿也是先供职于奥克兰的一家公立医院,研究儿童与青少年问题,家庭治疗对爱普斯顿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之后转到私人机构工作,人类学的背景使爱普斯顿对个体所处的社会关系较为敏感,同时,他关注文化对个人信仰的影响。叙事治疗法对仪式的使用就来源于爱普斯顿的人类学经历。
怀特和爱普斯顿都出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第一个生育高峰期,这一代人在童年时期的活动均不可避免地沾染了一定的政治色彩,成长过程中也伴随着一种对核武器及战争的恐惧,他们反对政治权力的统治,这一代人更有可能挑战现有的社会准则,这可以说是叙事治疗兴起的历史原因。两人对当时治疗界盛行的一些权威意识持反对态度。
更有趣的是,两人的妻子都是女权主义者,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很容易看到他们的妻子对他们工作方向的影响以及对他们的支持或是挑战。两人都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分别进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家庭治疗领域,当时,怀特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家庭治疗》杂志的第一主编。
从社会因素来看,后现代思潮的兴起,尤其是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的思想为叙事治疗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基础。福柯的影响涉及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从哲学、人类学到社会学。根据福柯的观点,将个体的生活故事与其生活本身联系起来是叙事治疗的关键。叙事治疗对传统心理治疗法提出了挑战,因为后者是实体论,是把当事人作为研究对象。其实在20世纪的后30年,随着家庭治疗进一步发展,已经有很多人表达了对传统治疗的不满,例如莱恩( Laing, R. D.)和反传统精神病学运动,主张将权力还给病人。另外,叙事治疗的兴起也得益于信息技术的进步,因为有了现代发达的信息技术,一种思想可以很快地传播到世界各地。
那么,为什么叙事治疗这一新的治疗取向会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兴起,而不是在美国或欧洲?这可能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历史文化有关。澳大利亚移民居多,很多家庭的孩子出生在一个国家,在另一个国家长大,成年后可能在两三个国家工作过,这样的体验可能导致以下两个文化特征:认同感的发展和对权威的怀疑。对个体而言,主要表现为对权威的挑战,例如种族特权、等级、性偏好等传统问题,这有利于个体自我认同感的发展。事实上,文化存在论是叙事学的基础,不崇拜权威、平等主义的文化传统与后现代思潮的结合,最终促进了叙事治疗法的兴起。


 正在提交中...
正在提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