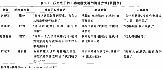(exceptions)的情形。当他们外出散步或者吃饭的时候,或许她和她的丈夫确实有过相当好的交流。于是,治疗师可能只简单地建议他们多做一些类似的活动。我们就可以看出解决中心治疗如何在建构主义顿悟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干预手法。
与解决中心治疗师类似,叙事治疗(narrativetherapy)通过帮助来访者重新审视他们怎样看待事物的方式来创造经验的改变。解决中心治疗是将关注点从现在的失败转向过去的成功,以便从自身的经验学习解决问题的方法;然而叙事治疗的目的更为广大、立场更加鲜明。这一模式决定性的技巧就是外化(externalization)——包括真正激进的重建(reconstruction)的方法去定义问题,不是视人为问题所困,而是将问题视为外来入侵者。于是,一个男孩总是不完成家庭作业,父母可能会说他懒或拖拉,叙事治疗师可能会问,在他和“拖拉大王”的比赛中,什么时候“拖拉大王”占上风,什么时候他自己胜了呢?
注意父母的建构———孩子是个拖拉大王———这是相对宿命论的;而后一个,拖拉大王有时候占了上风———将孩子从负面的自我中解放出来,将治疗变成一个和拖拉大王作战的过程。
解决中心治疗和叙事治疗采取积极角色帮助来访者质疑自我挫败的建构。他们都建立在我们通过与其他人的交流发展出自己的想法的假设基础上(Gergen,1985)。此外,如果有些想法使我们在自己的问题中不能自拔,那么在叙事重建的摇篮中会有新的和更有效的观点浮现出来。如果问题是人们学会对自己说的那些故事,那么解构这些故事必然能有效地帮助人们解决他们的问题。
批评家,包括我们自己(Nichols和Schwartz,2001),已经指出,通过强调认知维度的个体和他们的经验,社会建构主义者背离家庭治疗的一些既定的顿悟,即家庭是运作的复杂整体且心理症状常常是家庭冲突的结果。我们的经验和自我身份部分是由言语构建出来的,但只是部分而已。如果社会建构主义过于忽略系统理论的顿悟和忽视家庭冲突,那么社会建构主义就与家庭治疗毫无关联。40年前,Bateson、Jackson和Haley首先描述的那种两级化的互动——术语为互补(complementary)和对称(symmetrical)——可以被理解为同时反映了行为互动和社会建构,而不是只能两者取一。
意大利的精神科医生ValeriaUgazio(1999)描绘了家庭成员怎样自我分化,不仅通过他们的行为,也通过用“语义的极端”(semanticpolarities)方式来谈论自己。于是,例如,在家庭中,他谈论自己和他人可以区分为极端依赖和独立,交谈倾向于被恐惧和勇气来组织,需要保护或渴求探险。作为这样交谈的结果,家庭中的成员慢慢定义自己为:害羞的、谨慎的或者大胆的、有冒险精神的。■


 正在提交中...
正在提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