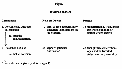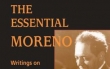研讨会
时间:2010年11月12日 16:00——18:00
主题:Lea Klein
主讲:张沛超
整理记录:李顺美
校稿:吴和鸣
张沛超:想讲一下师承关系,以表明法的纯正性。弗洛伊德传法于女儿安娜,终身秘书,主持翻译弗洛伊德全集,安娜总共分析了三个人,其中有一对夫妇,桑德勒先后接受这对夫妇的分析,本人又接受安娜的督导,并和她共同工作直至安娜去世。桑德勒支持犹太国去大学工作了五年,在此期间,仅允许两个人作为被督导者,其中一位就是克莱因女士。结束督导后,八十年代,她每月飞一次伦敦接受三年多的督导。对我的要求这么严也可能是传下来的。我本人的分析师的做法是介于老吴和督导师之间,有时三方力量就把人搞得蛮纠结。
在第一年的督导,差不多都是逐字稿。有一次我的被督导者有一个多月没见我,来了就说“你的头发……”,因为汇报的逐字稿,督导师就这句不显眼的第一句话进行工作,最后讨论时结论:第一层含义:在过去的一个多月,来访者在内心是保存了你的形象了,而且过去这一个月肯定想到了。第二点是,你的头发变化了,你还是不是那个咨询师?第三,我一进来就注意到你的头发变化了,在过去这一个月中我也变了你注意到了没有?我绞尽脑汁仅想到了前两层,在她提醒之后我的确也发现来访者的发型也变了。可以看到国外的分析师,漫长的师承传统中,对理解这部分的要求,都非常细致,跟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不一样,深刻、透彻。当然,这并非说他们做的不人本。接下来会看到她的案例。
这是网上找的以色列精神分析中心,希伯来语的她的介绍,是以色列精神分析协会的培训与督导师,是xx中心的创建者,所做的是动力性的分析、婚姻治疗、父母指导和危机干预。会场有个半中国血统,自称孟子后人的老外,而且说自己是哲学博士,而且是中国哲学博士,我说我们这儿的头也是专家。
在文章的开头,克莱因女士引用了现代派诗人艾略特的诗:我们所谓的开始通常是终结,我们所谓的终结通常是新的开始。结束的地方就是我们开始的地方。接下来他引用比昂的《网格图与caesura,caesura苏晓波写了篇文章。比昂在文章中建议大家研究撒修拉而不是分析者也不是分析师,不是无意识也不是意识,不是理智也不是疯狂,而是caesura,是连接是突触,这样一种既瞬间又非瞬间的情绪。在牛津词典中,caesura是停止、间断,音乐或者诗中的间隔。是这样吗?
肖燕:嗯。
张沛超:这样一个间断是为了强调一个概念,而且是要把诗或者节奏中的两部分连接起来,像个连字符。比昂是在弗洛伊德的1926年的《抑制症状和焦虑》中,谈到子宫内的生活和婴儿生活有更多的延续性。从未出生到出生之间是非常大的间隔,在弗洛伊德看来这个连接非常大,看起来是个caesura。他在自己的文章中提过一次caesura,比昂把这句话发挥了写了一篇文章。在比昂看来,要把不连续的部分连接起来,把生与死、分离前与分离后……胎儿生活与出生后的生活、东方与西方连接起来。比昂为什么要把东西方连接起来呢?因为比昂在八岁之前生活在印度。事实上我觉得她这部分理论综述倒不是很出奇,因为理论大家都知道。着重谈一谈个人的案例。比昂之后,科胡特、温尼科特都论述了这样一种间隔,事实上发挥了连接作用,克莱因女士治疗总是关注这样一些间断点。而且她为发展与创造力创造了一个新的连结。看第一个案例,她本人的。
这个人叫做Eli,在希伯来语中的意思是杰出的,事实上这个人非常不杰出。48岁,由于抑郁且有自杀观念而进行精神分析。他对他童年一无所知,而且似乎从来没有兴趣,完全隔离开,但总是重复着被压抑着的过去,治疗中的一个连字符把不知道的过去和童年之后不断地强迫性重复连接,在整个冲突中,有些时候我就感觉被冻住了,或者死寂的感觉。我变成了他那种难以承受的感受的容器。
他的母亲抑郁,在2——3个月的时候就被送到寄养家庭。这与中国很不一样,如果母亲有病通常由上辈人承担养育,而在以色列上辈人是不管的。每隔几个月就会从一个寄养家庭换到另一个寄养家庭。他成年后的生活充斥着分离,无休止的晃荡与抛弃,他本人抛弃了第一任妻子,又离开了第二任妻子和孩子,在不同的国家内来回晃荡,现在在以色列,还是不停晃荡。Eli非常帅气,声音低沉,说话的声调没有变化,治疗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像冻住了一样僵硬,说的都是生活中的细节,像某种没有生命的机器人一样,虽然他在说话但我感觉他完全不在场,而且他似乎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我,我能体验到这可能是某种防御机制。
Eli这样描述自己:我是一个只懂机械的人,我不理解人们,他们也不理解我。他也不知道怎么和人交往,对机械非常熟悉,他有爱好就是不断把机械拆了又合。在我们的会谈中我总在想交流在哪里呢?我们可以把机械作为一个比喻形容我们的关系吗?我很快的意识到真正的联系发生在非言语交流中。移情和对移情的包含,已经投射出很多东西,我就住在他的情绪生活中,在他非常安静、呐呐自语、完全与情绪隔离,我就觉得焦虑、紧张,有时候我高兴、兴奋,说的很快,语调变化很多。在有些时候我变得头晕眼花、犯困,整整四年我们都在转圈,他不停的告诉我生活中的琐事。稍后他告诉了我一个爱好,他非常喜欢木雕,尤其是雕成木碗,不同的大小和形状。我想到他不停的雕刻碗可能象征了他本人的创伤,碗本身就成了他的容器,但剩不下他的情绪,他从来都未停止过制造容器,这就是他同我交往的方式。
一个片段,发生在治疗中的第五年。出现了断裂点,重塑与融合得以发生。以下是Eli的自述:参加一个葬礼,案主是年轻人,从悬崖上掉落下来,掉到深渊,他不认识死者,但当谈及时表现了不同寻常的兴奋,尽管眼中有泪光闪动。此时我想到了就像拆卸机器时的那种兴奋。我意识到了他是在痛苦中变得兴奋。接下谈了一些细节。在停车的时候,他和女性朋友吵架了,她希望尽快停车,但他执意寻求更好的停车点。他说的很慢很安静。而我的内心非常汹涌,我进入到了一种难以名状且不断生长的躯体状态中,在此时,我也无法为自己的躯体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我的腿变得非常麻木,交叉又分开,想挪动不了。我在此时想,这点肯定有个威胁,因为内在的张力已经变成了头晕眼花,我问自己为什么如此不安?非常黑暗、空虚,且持续了很长。稍后我发现自己处于困境中。我没办法给身体找一个合适的姿势。此时我会想起了犹太人在死人时所做的悼文。
我跟他在一起,甚至是替换了他。到底是谁的葬礼呢?谁是那个死去的人?我不能动,空虚,甚至没有丝毫的念头呈现,无尽的黑暗。此次会谈中,很长时间我都搞不清我是谁。我听到自己的呼吸与说话,就像在深渊中一样,我逐渐变得漂浮起来。这时我的念头开始回来了,我体验到一种跌落的恐惧,坠落在地,而且摔在岩石上,这时吞噬性的焦虑、死亡,是他的。他居然一直生活在这样的恐惧中,真让人感觉可怕。
此时我说,你平淡的演说掩盖了非常槽糕的感受。关于如何停车的争论显示了你内在的争斗,你想为自己找一个合适的地方,那个从悬崖上跌落的年轻人粉身碎骨,让你联想到自己糟糕的感受,在你的真个生活中你从来没办法给自己找一个合适的位置,你就像是掉下,最后摔得粉身碎骨。他点了点头。保持沉默。我把这个与他的过去相联系。你从来未感受到自己安全,你总是被踢来踢去,而每一次的转移都像是从悬崖掉下你在深渊里与自己这个经历隔绝开来,此时他直视我,仍旧安静,接下来突然呻吟,强壮的身体颤抖、瘫软、放松。与此同时我也放松。我们就这样一直在沉默中到了最后。下次我们再谈的时候,他说他有个非常好的周末。他在他的车间中愉快的修正机器,想要愉快的换一份工作。他说的有些犹豫,似乎喃喃自语,又过了几次会谈,他非常兴奋且热情的告诉我,他的新计划,就像流水从山涧流入小溪,涓涓细流变成悦耳的声音。我在想,在那样一个断裂点,我们就在一起。当他心理上的死亡发生的时候,我做了他的一个容器,像怀孕一样,他在我的内在里成形。连接形成,新的生活得以开始。
先在这里停一停。在场的时候,听众反馈,当念到督导师坐不稳的时候,在场至少有五个人坐不稳。现场有一些互动,接下来有学员问,整整四年怎么过的,很难想象。我说虽然是两个人转圈,但不是一个人在圈里,有督导师陪着。同组姓孟的老外说还有很多人在圈里,那些抛弃了他的母亲们都在这个圈里。于是我说,是他们的鬼在圈里。可以看到克莱因女士的这个容器很厉害,我说如果是我碰到这样一个年轻人的话会非常无趣,我不会等他到第四年,可能很早就放弃了。这时,有师众反映,可能是投射性认同,他已经习惯了被抛弃,所以他一直等待着你的抛弃。另外有人说不是啊,四年中他都来啊。内心还是期望不是一个人的。我把这部分现场的互动也带给大家,可以先讨论一下。
吴和鸣:这四年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
张沛超:我也在想。他有个象征性的行为:把木头雕刻成碗,在停车的时候自己去找那样一个合适的点。可能治疗师的不作为就是当好了那块木头或停车位,就在那等。
吴和鸣:花四年的功夫把治疗师打造成治疗的容器?
张沛超:有点。
吴和鸣:换个说法。如果在第二年治疗师就给了这个解读会怎么样呢?
张沛超:我的体会啊,会不安,当一个人情绪隔离的时候,又知道他有这样一个经历,我可能不太允许自己接近死寂的那一部分。我们可以看到那时容器装的都是死寂,我想回本能的逃离。可能克莱因本人也会体会到不舒服,但悬置了。一直等到了对于这人的死的感受,以至于这部分力量送到督导师的容器里,把督导师也弄死。因为他已经灵魂出窍,本人出现幻觉,强烈的情感连接才使这部分空缺得以融和。
吴和鸣:压根儿就不是我们跟当事人的连接,而是跟自己那部分死亡连接。……
张沛超:你要死过,然后才允许自己再死。
吴和鸣:死过才能真正的与他连接。
张沛超:这样一个人就是一个死人。
吴和鸣:要工作很长时间才能把他的死亡体验传达给你。所以这四年就是做搬运工作……一个是他带过来了,另一个治疗师把它说出来了,就完了。后面治疗师说在子宫里成形,那个解释是成形的过程吗?我觉得还只是一个表达的过程,说出来就OK。
张沛超:后续的分析又进行了一年。而且他本人已经成为成功的商人,有稳定的家庭。起死回生的点很重要。
吴和鸣:如果没有亲历过那个葬礼,治疗师也没办法掌握恰当的意象去表达。
张沛超:我倒不觉得。来访者事实上不停地在说,可能过去的四年都谈了,如果不是葬礼,可能有别的比如产妇生了孩子,参加洗礼,于生死相关的非常多。
黄鑫:四年的时间他都在雕刻治疗师,每一次的倾诉都是一刀一刀的雕刻,不停地搬运死亡的感觉,经过四年的搬运,无形的气团经过葬礼变成了有形,让治疗师看到成形的意象。成形的点类似于终音点,又死到生,经过之后便有重生。治疗师强调的caesura,也可以理解为终音点,每一个乐曲和诗歌,在那个点都是方生方死、似有似无的。
第二部分
张沛超:下一个案例。五岁的小女孩。比昂提到了东西方的融合,我对教中国学生的体验:即使有这样大的差别,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人类的痛苦是一模一样的。由弗洛伊德所发展出的理论和技术可以供中国人使用,东方与西方就在此汇合了。May是一位中国小孩,由中国的治疗师治疗,所有理论基于西方。小孩在给的一堆书里,挑了《丑小鸭》,这样一个故事就成了治疗中的象征。她是在母亲怀里,母亲在汶川地震中死去了,当救助队发现的时候,她就在母亲的怀抱里。之后被转到心理咨询。起初她非常粘姨妈,但是沉默不语,不吃饭,眼睛没什么生机。最初,小孩会试图与治疗师近一点,但不会出屋子。当被要求挑选书时,就指了指丑小鸭。后来治疗师每次就给她读丑小鸭,仍不说话。
有一次就坐到了治疗师的腿上,指着说“红脸蛋”;治疗师反应:“就像你的红脸蛋,对不对?”她就把书合上了,离开了治疗师的双腿,爬到地上。督导师此时有个联想,爬到地上是作为治疗师将她与丑小鸭作对比的反应。丑小鸭也是被抛弃的。爬在地上像婴儿期的退行。过几周后呢,又指着那本书,督导师的联想是:我已经准备好了听这个被遗弃的丑小鸭的故事。我能忍受得了痛苦的回忆。第一次她呢能清晰地表述。她说丑小鸭的妈妈在河里游泳但是离开了,妈妈不想要这个丑女儿。治疗师问:丑小鸭是不是在不见妈妈之后难受啊?小女孩回答说:嗯,丑小鸭不得不自己玩。治疗师又问:妈妈会回来吗?小女孩不回答,而且扔了书,非常生气的说:不玩了。此时,督导师的联想是她以自己所理解的方式来讨论这场灾难,因为从小孩的角度,妈妈的死亡被理解成遗弃或者惩罚。与此同时,她有非常想念母亲,所以痛苦非常难以忍受,防御机制是隔离。
在接下来的几次中,她不说话,不再理会这个故事,更愿意去画画。起初是黑白的,后来逐渐有了亮色,从深蓝到红色,花了一架直升飞机,用黑色的笔把飞机画了叉,下手重,直到把笔用光,笔尖弄断。我们同她的姑妈做了澄清,原来她就是被一架直升飞机运走的,她对飞机很生气,在她看来就是这架直升飞机将母亲隔离开的。直升飞机就变成了一个坏家伙。在这个关于丑小鸭的投射故事中,她的妈妈抛弃了她,治疗持续进行,又回到了故事。丑小鸭的妈妈丑小鸭还在池边睡,所以就飞走了,丑小鸭不能飞所以不能找到妈妈。妈妈把门关了,但房子呢塌掉了,妈妈不能进这个房子,一个石头掉落到丑小鸭的头上,但它不害怕,躲在妈妈旁边,因为她知道出去就会被杀掉。此时她开始折纸飞机,而且说得更多,我再也不能见到我妈妈了,我被冲到峡谷里,妈妈被冲到了峡谷的对面。我爬上去找,但没有找到妈妈。妈妈没有开门,而且乘飞机跑了。我想用一个真的刀子把妈妈的飞机毁掉。
这个故事部分是投射性的,部分植根于她所体验到的真实。她妈妈的消失是很不解的,她对于妈妈的死的体验是抛弃了她,直升飞机就是鸭子的翅膀,在治疗中她第一次使用了这个字眼——妈妈。我在此呈报了一个感人的治疗,精致而发人深省。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漫、又不容妥协的过程,生命又回到了这个小女孩。通过这个故事她不断地抓取这个断裂点,不断地将被压抑的事件重新塑造,情绪被唤醒,逐渐修通与她死去母亲的痛苦的分离,这一次的分离被情绪式的处理了,所以她就没有变成一个石头。
这是第二个案例,最后是结论。
吴和鸣:现场对这个案例的反应是什么?
张沛超:现场没有更多的时间给这个案例。而且大家似乎对国外的案例——ELI更感兴趣。督导师说这篇文章在学会报告,大家对MAY感兴趣。
吴和鸣:这是连接,东方对西方感兴趣,西方对东方感兴趣。大家有什么感觉?
张沛超:每一次大灾难后这种故事都不是一两件。以至于很多影像都重合了。
……
吴和鸣:这个断裂点跟上一个断裂点有什么不同?这个是因分离创伤产生的断裂,那一个呢?参加一场葬礼?
张沛超:这个是Ⅰ型创伤,一刀剁。那个是Ⅱ型,慢慢磨的。
吴和鸣:那她说的caesura这个断裂是在哪里呢?
张沛超:在她所隔绝的过去和现在的不断重复之间的caesura。督导师的解释准确来说分成了三个部分。细细的看,第一个是:你这样看似轻松地描述掩盖了你内心非常糟糕的感受。
吴和鸣:压抑。合理化。
张沛超:督导师这样一个共情性的面质……
吴和鸣:这是个断裂,压抑也是个断裂,意识和无意识的断裂。
张沛超:第二个部分是,当前葬礼以及停车,与他感觉到像掉落了、粉身碎骨以及你总是在生活中想为自己找一个地方。这是治疗中的此时此地与当前事件完成一次连接。这时才与他童年时不断遭受抛弃……
吴和鸣:过去和现在的连接。
张沛超:嗯。这次就做了一个总的连接。
吴和鸣:这和我们说的领悟有什么不一样呢?可以把无意识的那段经历看成一个断裂,精分领悟是将无意识和意识修通。那她这有什么新意呢?
张沛超:她说要把这论文修改一下,投到国际期刊。她问我有什么建议。我说第一次看时觉得你在进行理论综述之后,Myidea部分太单薄了。但当我充分和你讨论这两个案例之后呢我又觉得论证已经很完好了。这两个案例本身就是对如何创造连接的很好的论证,但如果是投稿,理论这部分还要做一点工作。比方说Link的本质是什么?上次你不在,我借着王铭那锅汤下了点面,有个体会。读现象学,对内在时间感有点意思。我们的内在时间感跟钟表时间不同,是个纯粹主观的时间。
当我们有自体,这个跟内在时间感是同义词。自体就是围绕内在时间感建立的。Caesura是什么意思呢?就像骨头一样,有个点断了,要延续这部分时间感。骨科医生在接骨的膏药中要用到动物药,比方蜈蚣、虎骨、鹿茸,被称之为血肉有情之品。做一个药引,手术后筋脉尽断也要用到。我们在这样一个瞬间,当我们逐渐接近断点,我们本人也断了,为什么督导师在那一刻出现解离?在足够近的时候,内在时间感一同断。不仅是他的caesura,也是治疗师的caesura。治疗师在此点上做了正念。想到了过去一些事,断之前和断之后浮现了督导师的内部世界,她本人首先修复自己的caesura,然后才能送给病人。此点就发生了内在时间感的借用。
婴儿没有物理时间,甚至没有主观时间。当妈妈在,就是连续的,妈妈不在,婴儿就消失了。婴儿的时间感就诞生于,比如说温尼科特的抱持、比昂的容器,母亲尽管被孩子搅动,但仍去理解孩子的惊恐、焦虑啊,理解之后再送给她。孩子从母亲处借来时间感。孩子的自体从母亲的连续的自体借用而来,本人的时间感也是同理。所谓的血肉有情之体是在那样一个时刻,你们的时间感足够近,一断俱断,一连俱连。督导师、分析师那时要非常积极,要黏住,正念本身的意思就是系住、无妄。督导师要先活过来再连上。我说最好把Link同胡塞尔、海德格尔的两本书做一些结合,她起身就去找书,找到了希伯来文版。
黄鑫:治疗师应该割两斤肉做这个血肉有情之体,做药引子,否则就没多大新意。
吴和鸣:把时间从哲学上思考肯定是有意义的,但是把我们搞糊涂了。来简单一点。两个个案都涉及到创伤。创伤就是一个分离,时间消失了。创伤的诸多体验都是个断裂。治疗师的工作有很多层面,一个就是当事人大脑一片空白,所以很基础的一个层面就是复原: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去见证。这个是表层的连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连续性很重要。就是他的生活由此中断,那么我们慢慢的一步一步地给他连接起来。比如在四川,做这样一个连续性的工作就OK。
但对于有严重创伤的是不够的。治疗师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一样的分离,张沛超刚才说的很清楚了,他也跳出来了,治疗师经历了一个同样的分离过程。然后还把这个感受反馈给当事人。某种意义上就像接骨。当治疗师在经历这个过程的时候,把这部分讲给当事人听,完成了修复的过程。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对当事人到底有什么意义?张沛超的意思说是给他一个时间感。可是我的感觉是,在多层面的修复与连接。可能以前做的比较表层。创伤中分离体验的感受很深的那部分,原来是个断裂的,没有意识化,现在我们把它连接起来,这一段好像被抽空了的,现在给补充进去。
彻底的让那个人从分离中真正的走出来,需要我们去谈他的生活、事件的发生,最主要的是治疗师必须扎扎实实经历他那样的分离体验,然后告诉他。
李水子:如果是性创伤呢?被强奸了。
吴和鸣:你要有被强奸的感觉,体验一把,才真正到位了。就像我以前说的,一定要死过去再活过来。不然这个修复就不到位。
张沛超:有些时候我们没办法死过去,是因为对活过来没有信心,老早就跑了。
吴飒:我没有死,怎么知道那死的感觉?
张沛超:我自己的分析在暑假的时候断了一段时间,分析师过长假,起先觉得不是个事,本来自己社会功能就蛮好。在分离后的第一个月结束的时候,内在的抑郁、愤怒,理不清道不明的烘烘上来,又感冒又拉肚子又睡不着觉,才真知道分析有多重要。等他回来之后好好扯了一把皮。
陈爱华:跟苏晓波以前写的文章《成为病人》有点类似。
吴和鸣:是啊,苏晓波就是受比昂的影响。
张沛超:苏晓波说“治疗就是两个人呆着”。可能在那样一些时刻到来时或之前我这边呆不住了,没法呆了。
吴和鸣:后面呢?
张沛超:做了一些升华,引用了美国一个分析师的话,我查了一下这个人很有意思,写文章经常引用佛教文献。动不动就引用一段《楞伽经》:重生的要点主要是一种节奏、旋律,包含了混乱和连续。温尼科特认为混乱也是更深层次的连续。有一些伤痛是永远没法疗愈的,甚至是不该疗愈的,甚至这样一些痛苦可以成为走向更好的动力,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人。对创伤的修复过程,在进化中被标记成为一种重生的幻想。远古的童话和故事都描绘了创伤所带来的后果,变成石头、魔鬼,一朵花或者贝壳。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法,这些痛苦一次又一次被经历、修通。有一些新的东西发展出来,一种开放、复活,向着更好地方的行进。在阻断和流动、创伤和新的开始之间,总是有着永恒的运动。引用了泰戈尔的一句诗:不要试图填补生命的空白,因为音乐就来自那空白深处。打断是更深层次的连续性的标志。
黄鑫:泰戈尔的原句是“让音乐从生命的空隙处涌现”,不是“因为”。它是接纳性的。
吴和鸣:完了?
张沛超:完了。之前的理论概述部分大家基本上都知道。
第三部分
吴和鸣:苏晓波在讲caesura的时候是指不确定。而她这文章的主题又在连接上面。很奇怪。
张沛超:一个人只有知道蛮多确定的时候才能忍受、接纳不确定。所以苏晓波说的是上乘的果位,并不是说生活中大家的不确定都不要处理。对一个入门的学生来讲,用处不大。
吴和鸣:她这个题目是什么?
张沛超:分离与连接——从间断点到一个新的生活。那四年的时候不是充满了不确定?
吴和鸣:都是日常生活的细节,治疗走向何处不确定……什么时候会出现治疗师的分离?是不确定的。
张沛超:如果你听了这样一个人的案例,自己心里琢磨,早晚都要死,但什么时候让你死是不知道的。
吴和鸣:从另外一个方面说这个意思,我觉得她忽略了另外一个层面。以前在学校里做督导的时候,我用了一个比方:有一个人走着走着,掉到一个坑里了,好辛苦的爬起来,假设这一段是莫名其妙的,但继续往前走,再遇到坑坑洼洼的就小心翼翼,一些分离反应就出来了,严重点PTSD都出来了。现在他来找治疗师,治疗知道了是个什么事,就是确认了这件事。而这个人发现别人跑前面去了,我要追赶啊,怎么办呢?我们说先前要去哪还是可以去,就是慢一点等等。现在我们做一下神入,掉下去的时候,一片漆黑,很孤单、恐惧,好不容易爬上来又滑下去了……这些分离体验我没有经历完全可以说得出来啊。好。现在当治疗师在治疗的时候也掉下去了,说明治疗师本人有创伤,或者通过这个治疗在疗愈他的创伤。我要说的是这部分。
张沛超:这倒提醒我了,督导师母亲这边除了她母亲这支,其他的都死在集中营里了。
吴和鸣:所以是病人在追悼会上带回来的东西激活了治疗师本人的创伤。实际上通过这个治疗,她治了一把。这是典型的相互治疗。
张沛超:很多犹太人伤都没好。
吴和鸣:这也是今天特别强调犹太人这个背景,很有意义。
张沛超:我有一次报案例,小孩提到了长大后要当希特勒,督导师一眼就看到了希特勒这个词,就像认知心理学的启动效应,我可能就看不见。
吴和鸣:还有,往往创伤的意义在哪里?假如没有中断,就看不到本来的连接。因为创伤,断裂发生,更深刻的感受连接的存在。所以创伤是种发现。没有创伤,就不会发现人类对于创伤有如此厉害的防御、保护策略。通过创伤来发现自己。
张沛超:你这么强调这点,大家早死晚死,都得死。
黄鑫:可不可以把苏晓波说的“不确定性”理解为终音符?苏晓波说的是真空的层面,督导师说的是妙有的层面。不确定是真的空,但呈现的时候需要有形的东西,就是妙有。通过创伤有了连接。
张沛超:今天这个气氛有点沉闷。当时报的时候有点闷,但后来的讨论还蛮热烈。
吴和鸣:讨论了些什么?说说看。
张沛超:就是我刚才说的。
肖燕:根据音乐来想的话,caesura是休止的意思,但休止是没有声音的,想到了指挥家,指挥家是背谱子的,一个声部停下来了,其他声部在动。治疗师需要把当事人变得丰富,这个声部是休止了一段时间,但其他声部在走,连续起来,不同的声部在演奏不同的旋律,这样才能达到整体的效果。这个人是掉坑里了,继续走,站起来走的时候就像演奏不同的声部,过各自的生活。
张沛超:作为指挥本人要背谱的,但即兴演奏,没谱。治疗有点像,不管学了多少经,总是感觉没谱。每一次就是一次即兴演出。
……
张沛超:这个跟我们以前讨论的故事,治疗师要装够故事,心里就有谱。卡壳了,知道往哪走。脑子里要有足够多的谱。
杨玲:想起黄真伊,艺妓,没有音乐,她自己跳,乐师没谱,随着她的舞蹈演奏。
肖燕:我的当事人演奏了音乐,我如何跟她合拍?所以治疗师也需要即兴演奏。
张沛超:我在想一些高明的舞者可能脚下滑了一下的时候,动作纠正后变成了新的舞姿,跳起来不踩脚,看起来蛮玄,但美。治疗也是,即使摔了一跤,也还是该多跳。对于Eli这个个案,你觉得他在哪个地方断了?
肖燕:我也在想,休在哪里。
张沛超:主动求治的人一定有个声部完整无缺,哪怕负性治疗反应多得不得了,总有个主旋律——生本能是没断了。
吴和鸣:还有什么想说的?我在听《存在与时间》的课。比如“在世界之中”,至少有三个。一个是世界是什么?谁在世界中呢?最后是“在之中”。花了很大篇幅比较了“在之中”与“在……之中”,比如黑板在教室里面,笔在黑板上,都有清楚的位置,相互的关系。但那个世界都没有规定的时候,你凭什么说呢?……我们把它变成“在之之中”,有个东西,但没有得到规定的时候是不能够这么说的,只能这么讲“在之之中”。我想到治疗师和当事人,治疗师在此在的状态,四年的时间都在被治疗,病人也在之中,都在各自的世界中。现在我们看见的是两个人坐在治疗室中,实际上每个人在此在的呈现过程中,那个点,我觉得是共在。各自在那个地方,一起到那个点上完成一个过程,可能治疗中的片段都是那些个点。这个我说不清啊。
黄鑫:在之中,就是在当下之中,就是每一个当在,四年之后两个人的当下融合成了一个当下。
吴和鸣:不光是当下,其中有世界、有我属性。简单地说不是我在病人旁边,是你在你旁边。
张沛超:两个人一起寻找在什么之间。比如在那个间断点,治疗师要考虑究竟在什么之中,哦,原来是重复过去的事情,不知道在什么之中就在之中。事故是在之中,故事是在之之中,之是脉络、情境、维度之类的。
李顺美:我倒觉得不一定要找个什么点让两个人呆一起,重要的是两个人都在。
张沛超:你在我之中,我在你之中。
李顺美:两个人同在,在流动的某个点等着有共时性的东西出来。
吴和鸣:谁在等谁啊?谁在治谁?很难说。
黄鑫:只是说在她刚才说的共时的那个点两个人的当下融合了,并不是说是个同样的当下。各自的当下是平等的。
张沛超:我估计这个病人要是找老吴的话用不了四年。老吴说我死,你看那坑在哪,埋。
吴和鸣:你的意思是我的创伤就没有机会治好?哎……


 正在提交中...
正在提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