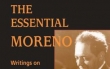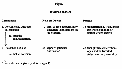设置、病人与诗
来源:华中子和心理咨询中心-精神分析联合机构
主讲人:王光
整理记录:李顺美
校稿:吴和鸣
王光:这好像和刚才的督导相关,对治疗设置的反思,对治疗过程的反思。大家有什么想法?
李顺美:治疗设置真的很重要,它的打破往往有很多象征的意味,而且,这种打破是无以复加的,就像一个漩涡,一旦打破就会陷进去。
王光:说得好。
齐华勇:记得有一次,吴老师讲,要看这个设置是怎么被打破的。
王光:在一个牢固的有序的协议框架内才可能保持心理治疗的过程。认同吗?吴医生?
黄帅:吴老师,你认同吗?
吴和鸣:这是真理啊,同志们。
吴江:谁的真理?
吴和鸣:这是多少代人的治疗师通过血泪教训凝固起来的真理。
王光:但是我看上次研讨会的记录,你好像是要颠覆,设置这一块。
黄模健:我和王光是同感。
吴和鸣:我们来看看,那天的讨论哪个部分颠覆了设置。有吗?三百块钱没有变,场地没有变,时间没有变,什么设置变了?没有啊。
大家:角色变了。
吴和鸣:角色变了那也不是设置啊。对不对?
吴江:这就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有角色才有设置。或者说有了设置就有角色。这两个是在一起的。
黄帅:这句话真是精辟。
吴和鸣:怎么讲?
吴江:我有这个角色,就按这个角色行事嘛。比如,一个老师,就要讲课,家里的事怎样先不管。
吴和鸣:你看啊,你说老师一定就要有角色,对不对?
吴江:对。
吴和鸣;你是医生就一定有个病人。这个角色有什么不一样呢?你说有角色就有设置,难道是因为有治疗师才有设置吗?没有病人你哪有设置呢?
吴江:嗯。有角色就有了要求。
吴和鸣:设置是对病人的要求吗?是对双方的要求。
吴江:是。
吴和鸣:而且是共同制定的。
吴江:是。
吴和鸣:这跟角色有什么关系呢?
吴江:共同制定的是单数还是复数,是此时还是整个历史?就有个区分。比如说我和我的咨客此时的角色确定了,但是,我是一个医生,背后有这么大的一个群体,这个角色固定在这个地方,所以既要去满足此时的角色也要满足大的背景的角色要求。
吴和鸣:你说的这个角色是指当医生和当老师的不一样,是不是?
吴江:是。
吴和鸣:好。当医生的话,治疗有特殊的要求,有治疗的设置。一旦进入治疗的时候到底是谁来规定这个设置呢?
吴江:当进入的时候已经有规定。
吴和鸣:这规定怎么来的,从历史上?是哪个拍脑袋想出来的?
吴江:哪个拍脑袋想出来的是个鸡和蛋的问题。
吴和鸣:那还是和角色没关系啊。
吴江:但不管怎样,已经有蛋了,我们为什么要探究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吴和鸣:关键不在这个,就是说我没有颠覆设置。这是肯定的。
吴江:颠覆了角色。
吴和鸣:那角色和设置没关系。
黄帅:吴老师,你上次说设置是背景,那背景里最稳定的应该是你作为治疗师的角色啊。
吴和鸣:何尝你的当事人不也是一个稳定的角色呢?
吴江:那这样讲,就是两个灵魂吧。没有设置,也最不需要讲设置。
张沛超:天啊,两个灵魂坦诚相见,多么感人啊。
王光:好。这个我听懂了,老吴胜出。看下面的,外部规则,解释心理治疗师做什么的,其次是治疗持续的时间、治疗的次数、费用、关于中断的协议。内部规则是自由联想和自由漂浮式的注意,第二是节制。分析师不应满足他或病人的需要或愿望。能做到吗?
吴江:这个是有意识的。
王光:无意识的哪知道啊。
黄帅:自由联想和自由漂浮式的注意,怎么理解?
张沛超:老吴完全可以把这些都否定,说太理想化了,不符合中国国情。
吴和鸣:那是你在说,不是我在说。
王光:悬浮注意让张沛超讲一下。
张沛超:精神分析讲究自由联想和悬浮注意,但我们并不总是能够自由联想和悬浮注意,但当我们做不到这些的时候可以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就是在自由的间隙,被束缚的注意是最重要的,究竟发生了什么。
黄帅:什么是悬浮注意?
王光:就是一个观察的自我,去看。
齐华勇:第三只眼。
王光:这些在精神分析词典里都有,大家可以去看看。节制,怎么节制?
吴江:还有没有其他的规则?这个自然是最重要的。
王光:你假设还有什么?
吴江:不知道啊。
王光:大家想一想啊。还有什么其他的规则。
吴江:为什么精神分析这两个是最重要的?
王光:我觉得自由联想和悬浮注意不一定摆在一起吧,自由联想是一个方式……
张沛超:自由联想是病人躺在那里,悬浮注意是分析师的。
王光:以前吴老师讲精神分析艺术的时候很强调分析师的自由联想。
张沛超:我们可以把分析师的自由联想看成是完成一个自己的悬浮注意。
李顺美:那如果自由联想出来了是不是要节制呢?比如分析师的很多需要、想法出来了,他这个时候要去考虑设置吗?不是要自发性的去做吗?那这个节制指的是什么呢?
王光:嗯,这个问题问得好。怎么回答?就是我们无意识的那部分也要节制吗?
吴江:节制属于主观层面的。这一切都是主观的,我有意识要去做的。而无意识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张沛超:在节制的问题上,拉康有一个见解。他把欲望和需求分开了,欲望是desire,需求是demand。如果一旦我们满足了他的需求的话,这个需求就没有了。但是一个desire永远指向另一个desire。我们不满足这个表面上的desire,然后一个desire连着一个又一个的desire才会出来,要不然,来一个满足一个,就把他的欲望封起来了。这看起来是一个满足,事实上对深层次的欲望是一个挫折。难道他仅仅是想抱你吗?不是,背后想要的是更多的desire。我们不满足demand才能真正让desire释放。
王光:是,这个外部规则很清楚,关于内部规则,我们脑子里的这些东西怎么节制,如果是需要的话就可以节制,如果是欲望的话就不一定能做到,对不对?
吴江:讲的是病人的需要与愿望,不是欲望。
王光:我是说分析师。
吴江;是啊,可以满足他自己和病人的需要和愿望,这是意识层面的。
张沛超:拉康对分析师的欲望的解读,分析师不是没有欲望,他的desire就是让来访者自己的desire,为什么分析师需要有这么一个很强的愿望呢?因为病人的症状形成后有一个妥协形成,所以有一个很大的获益,无论是初级还是二级。他觉得很舒服。只有分析师不断地希望看到他的desire的时候才能使他放弃这些获益,来满足咨询师的desire。而满足咨询师desire的过程中,他自己的desire才真正的自由起来。
王光:好,举个例子,比如说在治疗的过程中,我们谈分析师的节制,突然一个病人,我看到他之后有一种欲望,有关性的幻想,在那一刻,我怎么节制?
吴江:最好的办法是把它当做他物。
王光:他物,怎么说呢?
吴江:就是我所有的这些反应都是跟治疗有关的,或者说我处在分析师的位置当中。
王光:就是还是回到设置上来?
吴江:在这个位置,所以这个反应是跟我有关的他物。
王光:那这是不是一种防御呢?
吴江:那你怎么办呢?满足?
李顺美:那如果明明是自己的欲望,却说是来访者引诱或者说是关系的需要,岂不是给自己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
吴江:容易这么理解,比如说我这个欲望是跟他有关还是跟我有关是我的事情,但位置还是在这个位置上。
黄帅:说的是节制啊。节制和完全的压制还是不同的。
吴江:如果你能意识到的话,那就不是一个完全是什么,单纯是什么……
张沛超:比方我们上了高速路了,如果两边都没有护栏,自由不自由?
王光:危险啊。
张沛超:非常不自由,很危险。如果两边有足够高的护栏,反倒自由了。
吴江:所以越是设置严格越自由。
张沛超:从动力学上,这个设置意味着什么。比如现在这个治疗关系非常亲密,有时候亲密呢就跟谈恋爱一样,有时候亲如母子,有时候又有很多冲突,像谈判、下战书。就是说它像这个又像那个,但是有一点,它既不像这个又不像那个,它是治疗。再者,动力学上,设置是一个父亲的名字。小男孩长到俄狄浦斯期,说妈妈我以后要和你结婚,妈妈会有两种反应,第一种,那怎么能行呢?小心你爸回来揍你——连欲望带需求一起掐了。第二种,你要是和妈妈结婚了,那爸爸怎么办呢?如果没有父亲的名字存在,孩子没法从母婴的共生体中成长出来。
王光:所以在治疗里,什么叫刚刚好的节制?举个例子,病人与分析师要共振,如果在这里分析师也觉得兴奋、喜悦、满足,我们的分析师可能会想他让我觉得舒服了,我不应该这样。另外一种观点,我不放松的话,那么这一部分带给病人,他也可能不放松,那么什么样的是一个刚刚好的节制?在那一刻可能我们两个都很舒服。
张沛超:考虑一下,什么叫刚刚好?
王光:如果设置太严格,可能就把他自发性的一部分压制了。
张沛超:我们在评判一个东西刚刚好的时候,更倾向于,比如英美法系,大陆法系,不是一个先验的立了一个规矩,叫刚刚好,可能是以前过了一点,对两人都没好处,所以成为了一个案例、参考。而今天的设置就是由于以前晃来晃去搞个两败俱伤,所以今天形成了一个经验。
吴江:能不能具体一点?刚刚好是这次从进门到结束一直都刚刚好,还是治疗的每一次都刚刚好?
王光:那是强迫,怎么可能呢?
吴江:那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
王光:想起以前一个老师来中国,他讲他和那个病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喜欢爵士乐,那个病人也对爵士乐有研究,有那样的片刻,两个人有共振,都觉得舒服。那是刚刚好,对不对?
杨玲:好像就是可以去,也可以回来。
王光:(看老吴)在想什么?
吴和鸣:都讲的蛮好。
张沛超:这是刚刚好,如果后来拿出两张爵士的票,说要不做完治疗咱俩打的去吧……
吴江:破坏设置。
黄模健:刚刚好还有一个底线的问题,如果去看那就是打破设置。
王光:是,就像恰好的挫折。只能是个片刻,如果从头到尾,只是个理想的状态。
某人:这个刚刚好不是要去追求的,不追求就是节制。
王光:是,发生的。
吴江:那接下来我们做什么呢?
王光:享受?
吴江:不是。比如在那一片刻我有刚刚好的感受,他也有,接下来50分钟做什么呢?
张沛超:这哪是一个问题呢?接下来自由联想继续啊。
吴江:那这个治疗师的状态是有变化的。大部分是另一个状态,有时候会有这样一个状态。但觉得这样的是最好的。
王光:我们去拓展那一种感受,不是刻意的拉回来,而是无限的延伸拓展。两个人慢慢试探着去感受。在不断的拓展这种感受的时候,也许他自发性的东西就会出来。
吴飒:接下来做什么不是说治疗师,而是就是自然地发生了。
王光:是。
李顺美:也许刚刚好的状态是很瞬间的,但更重要的是背后的意义,为什么这个时候刚刚好,两个人各自触发了什么使得刚刚好,这就是一段关系嘛,可能这个意义更值得探究。如果说后面做什么,可不可以就这个刚刚好来探究?
吴江:治疗大部分是在用力,有一个时候是在用心。
王光:有可能就像一个孕育的过程,之前需要两个人共同努力,创造一个恰好的环境,孕育之后孩子出生,就是一个创造性的成果。是吗?
张沛超:这一刻刚刚好。
邵彩宏:我在想刚刚督导的那个案例,咨询师不敢去表达自己的不舒服之类,她这个表现其实不是节制,但是在我们看来就是节制。
张沛超:这叫憋。
李顺美:如果那不是节制又是什么呢?我想保证这个设置啊。
万晶晶:我觉得她的做法就是一种节制,她觉察到自己的这些不舒服的情绪,没有像社交中的直接表达,而是控制住自己,没有顺着自己的情绪来。
张沛超:这个节制是有一种忍的成分。但是不能为了节制而节制。就是她在装了这些情绪之后,如果仅仅把它压着,而不去考虑,或许你也会出现同样的躯体症状。这样你们俩就共同错过了一个看desire的机会。这个对双方都是没有意义的。在我看来,精神分析事实上重新延续了一个非常好的传统——认识你自己。症状的缓解就是追求一个认识,再认识。所以当这个“不舒服”来的时候,不能忍啊忍啊。
李顺美:还是要一起去看。
张沛超:是。
王光:精神分析总是要探求原因或者往回看。现在我们看病人发展的那些部分,其实跟人本是相关的,对不对?这怎么去整合呢?
张沛超:这一块老吴最有发言权。
王光:精神分析就是回到一个孩童、婴儿的状态,很本真,那如果让他发展,结果会怎样,指向的是一个什么东西?
吴和鸣:你觉得呢?
吴江:你这样的一个表达是期望有一个自发的东西,但是进入治疗,就会被打上烙印。
王光:发展了,最后回到原点,和精神分析的原点是一样的。
吴和鸣:这本身就没什么区别。说到设置,有很多基本原则,一个是说平衡。我们说的自由联想、退行、前进,全部是要有一个平衡。不是部分的强调哪一边,而是做平衡工作,那么设置怎么来的呢?设置的定义就是一个合同一个协议,合同是我以往的经验,包括整个治疗界的经验,把我们可能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冲突,先把丑话说到前面,就定为设置。然后我们说的平衡,不是偏向哪一部分而是两者之间的平衡。另外一个,你怎么节制?有另一个原则,设置怎么有助于个体的发展。比如神经症病人相对要保持更多的节制,那对于BPD,你要增加对他不好的情绪的容纳的时候,也要有一定的节制。你的方向很清楚,怎么有利于个体的发展,所以发展是硬道理,怎么有助于他的发展。一周几次可以调整,为什么要有调整?就是有助于发展。
王光:还是要看他的对象,然后灵活的掌握。
吴江:那跟欲望有什么关系?
吴和鸣;当然有关系。刚才张沛超说拉康说的那个,治疗师始终有一个欲望,这个欲望是什么呢?探究的欲望。要探究自然就会有节制。因为满足了就没有探究的可能了。然后呢,治疗师也有一个强烈的助人动机,让他成长,而且这种成长是可持续的,不是眼前的拿个高分数。
张沛超:有一个矛盾在理论和临床上都没想清楚,精神分析有一个很关键的治疗就是促进退行,在哪里跌倒在哪里爬起来,退回去是为了更好的前进,但是退到什么地方算够呢?
吴和鸣:这是你可以操控的吗?
吴江:就是说什么样的退行恰恰好?
张沛超:理论上好像也没人探究,退到哪刚刚好?
王光:还是要看对象。
吴和鸣:治疗师病的越厉害,病人退行就越厉害。
王光: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
张沛超:老吴的这句话里蕴含了非常多的情绪和思考。
黄帅:是不是说精神分析的话,病人一定要退行?
吴和鸣:只要是人就会退行。人总在退行和前进当中。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就退行到了子宫,早上起来就是一个婴儿,上班的时候就成了一个大人。每天都在循环往复。
齐华勇:应该出一本书,老吴疗法句读。
吴和鸣:退行是无处不在的。是退行与前进中的平衡,没有绝对的。比如说自由联想让他退行,但不能光自由联想,还要跳出来。
王光:嗯,悬浮注意。
吴和鸣:不论是治疗师还是病人都要这样。这就是平衡。
王光:还是那个,为什么治疗师病的越厉害,病人退行就越厉害?
吴和鸣:比方说你有拯救情结,你有控制的需要……
王光:又被你(张沛超)打断了,还没说完。
吴和鸣:说完了。
张沛超:我在保护老吴。
吴和鸣:你这个保护是什么意思呢?他比我病得更重,不想让我退行。
李顺美:吴老师刚才的意思是说,如果治疗师有控制感,病人就更依赖。
吴和鸣:肯定啦。他凡事都去控制、指导,没有我你活不了,对方就退行了。
黄模健;吴老师,我有个案例,感觉他退行了,把腿绑在沙发上,一种很放松的状态。
吴和鸣:是啊,你看,他来到治疗室,一开始很紧张,到现在比较放松,放松的状态是一种比较安全的状态。安全就不用戒备、警惕,没有后顾之忧,他敢于去相信治疗师。退要看退到什么程度,能不能回来。
李顺美:那如果退不回来呢?依赖上治疗师了。
吴和鸣:那就是问题啊。
张沛超:我来做个句读,为什么老吴说治疗师病的越厉害,病人退行就越厉害。在正常情况下,每个人从家庭中下来身上都有一个鬼,客不夺主位,闹腾闹腾但不夺主位,客是邪,但是客有点要践主的味道,怎么办呢,原来主要把这个邪封起来,但是在治疗这个环境中,终于感觉到不要紧,有人能降这个邪了,所以就解封。治疗师这不光是个人的邪,而且有一堆邪,不同的来访者,使外邪引动内邪,但是治疗师的功能比较不错,来访者就感觉到他有这么多邪说明他的降魔经验是够的,二来本人功能不错,说明我可以把邪交给他来驯。
王光:那还是治疗师的经验。
张沛超:是,治疗师的经验并不一定是个人的经历,还有集体无意识的原型,以及来访者传染的。以至于治疗师病得都疯癫起来,这些客团结在主的周围,随时准备接应这个邪,降魔的过程无非是搞清楚因果,你看西游记那么多妖怪,那个被杀了,没有,如来佛前的灯芯,回去;观音的狮子,回去。治疗师的降魔过程不是杀,是搞清因果。这些降的魔啊,就成了老吴身边的,要么是茶杯,要么是座骑,要么是花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他这儿的东西越丰富,他一看这东西的来路就越清楚。
王光:我想起以前苏晓波写的“成为病人”,结果那天,他说,以前我成为了一个病人,现在我是一个诗人。
张沛超:当代诗人的同义词就是疯子。
王光:就是凤凰涅槃了吧。
吴飒:那是不是治疗师病得越重越好呢?
张沛超:那不见得。如果治疗师这是客夺主位的话,这个邪不仅没被降服,反倒沾到他身上了。
李顺美:可能是说他曾经病得很重,现在功能很好。
王光:他有一个消化的过程。消化好了之后他就成为诗人。
吴和鸣:你对苏晓波说成为诗人有什么想法?
王光:我在想,他的心理面一定是经历了一个过程,作为一个诗人会有很多什么样的感受?作诗的话应该是有一些兴奋或者享受的。
吴江:诗人是指的什么?定义是什么?
王光:没有一个定义,你认定的那个诗人和我心里的是不同的。就是说我们的感受会不一样。那两个字不重要,重要的是带给我的感受。什么感受说不清楚,可能是一个意境什么的。
吴江:内心是一个诗人。
王光:是。
吴和鸣:你怎么理解?
王光:内心是诗人,我现在可以作诗了。
吴和鸣:诗人和病人有什么区别?
王光:病人我身上全是邪气。诗人的话在邪气的外围有光环。
吴和鸣:诗人的状态和病人的状态有什么不一样呢?
王光:诗人的状态有更多美好的东西,那样的治疗有可能就是一个艺术。
张沛超:有什么不一样呢?病人事实上也在写诗,是以症状的形式写出来的,诗人是以语言的形式。症状不像语言那样具有非常好的主体间性,它只是一个蛮孤独的东西,没有听众。
吴飒:诗人把自己的痛苦写给其他人看。
吴江:诗人的片段。
王光:他讲,我以前是一个病人,现在是一个诗人,那么内心肯定有一个心理的过程。我的理解肯定和你们大家的不同。
吴和鸣:这叫什么?
吴江:不要那个人,只要那个诗。
吴和鸣:回过头来讲,比方说,自由联想怎么成为了一个设置呢?自由联想也是一个技术啊。技术和设置怎么放到一起了呢?那到底是技术还是设置呢?
张沛超:和尚修禅内观的时候也是一个自由联想。它也有设置,不能做到大街上,或者中午吃了一大堆回锅肉啊。设置就像高速公路的护栏,两边架好。
王光:设置是外在的,内在是自由的。
吴和鸣:我们刚才谈了那么多内容,都和节制有关系。当初苏晓波说成为病人的时候就是说我是某一个病人,成为诗人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不是这个病人也不是那个病人,不知道是谁。诗人就是说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精神分析的艺术强调的是瞬间,片段,每一个流动的过程,所以学精神分析讲精神分析都不好讲,要像诗人那样讲才行。像诗人那样去做才行。没有那么多可以确定的东西。
张沛超:当代为什么病越来越多了?当代是一个诗人没有地位也没人会做诗的。
吴和鸣:不是这个意思。病越来越多,此刻我作为一个诗人,来了一个病人,我就给他写了一个病名,张沛超来了,我又给他写了一个病名,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没有那么多相同的东西,都是此刻我灵机一动给他下的,就像上次谈中医的,这才是真的符合人性的东西。每一个治疗瞬间都是流动的,都是在写诗。
齐华勇:每刻都是诗。
吴江:也是一种加工中的诗。
张沛超:尽管写诗,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诗里面都还要押韵、平仄,这又看出来设置。
吴江:海子有一个普遍与众多。就是说,之所以我要有一个状态是因为有众多的人在那里,所以我要寻求这个东西,束缚个人的,所以要去打破。
王光:还有一个根源是,我有一个什么样的眼睛,在我看来这是一朵花,可能别人看就是……
张沛超:牛粪。
王光:看我带着什么样的眼睛去看。
吴江:而恰恰后面的才是人生的状态,真实的生活是这样的。当你看到花的时候,很多人说错了,那不是花。
王光:那跟我没关系了。
吴江:但你生活在这样一个……
王光:那你这界限也太不清楚了,凭什么说这是牛粪你就认为它不是花而是牛粪嗯?
吴江:大家都说是牛粪啊。
王光:那是他们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
吴江:那就是你疯了。
吴和鸣:……用疯癫对抗疯癫……(略)
王光:如果我是一个犯了一点点错误的人,然后把我抓进监狱了,监狱的人即用酷刑来对待我,我就变成另一个不一样的人了,更疯癫。用更坏的东西来对抗秩序、法律之类的。就是说我变了。
吴和鸣:这就是你的经验范围内,你的理论告诉你的东西。但现在这就是一个完全不确定的。你可以带着 这些经验和背景试着去探索,但最终中间的那个空间绝对是超乎你的想象。
吴江:……(略)
吴和鸣:第二个疯癫。用来对抗他内部的疯癫状态。他里面的疯癫是什么呢?不是不可知,是可知的,我想说的是,没有一个重复的一样的,经验的东西只能作为一个背景,那今天这对我来讲就是一个颠覆啊。我看到了分裂背后的分裂。
吴江:一定要有一个指向的。即使不知道,但所说的必然有一个指向。
王光:所指就是内在的人、关系或其他的东西。
吴江:这又是你的经验。你的经验跟他的经验是不一样的。他所指的是什么?
王光:是啊,那么我们永远也不知道。我刚想到,以前在坐电梯的时候遇到一个人,他的牙齿是很厉害的外暴,刚看到的时候我吓了一跳。
吴江:……(略)之所以用这个来对抗那个东西,那就是有匹配的。他为什么不用其他的呢?他还是在借助人的方式啊。
吴和鸣:……实际上是一种诗性,这是诗人的行为。非常有创造性的。
吴江:那个疯癫也是带有人性的。人的方式去对抗一个人。
王光:那还有用大便在墙上画画呢,那也是艺术。
张沛超:我不知道老吴对这一举动有没有充足的澄清,……
吴和鸣:……
张沛超;老吴评价会说是一个非常诗意的行为,但是任何人作诗是有对象的。作诗从来是希望人读的。在老吴这里就成了一个诗性的动作,如果是跑到一个素有洁癖的医生那,估计要上一堂健康教育课。人家不懂诗嘛。
王光:所以如果我们不用自己的经验的话要怎么去活?
吴江:按习惯。
王光:自发?
吴江:习惯。
王光:我要把那个故事讲完,在电梯里,看到他后吓了一跳我就躲到旁边来了,就是牙齿暴得非常厉害,然后他故意绕到旁边故意把嘴巴张开,故意吓唬我,当时我就想,不用心理分析去分析这样一个现象,我就自由联想……这是怎么样的一个疯癫?第一个疯癫只是吓了我一跳,第二个是大大的吓了我一跳。
张沛超:看你面善啊。
王光:他肯定有内在的心理过程。
吴江:不在于他的疯癫,而在于你,你看到的这些意味着什么。
王光:是。
黄帅:原来我是病人的时候,我的病人是病人,那现在我是诗人,我的病人是什么?诗人?
张沛超:属于连续培养项目。
吴和鸣:你从来没有看过这种牙齿的人吗?
王光:没有。
吴和鸣:你也从来没有遇到过他在吓了你之后再次给你一个吓唬?
王光:是。我没见过。
吴和鸣:那就是,他是独一无二的。
吴江:不是他是独一无二的,而是我感受到的这个东西是独一无二的。
吴和鸣:行为艺术。
齐华勇:吴老师,您的意思是那个露牙齿的在王光这里也是独一无二的?
吴和鸣:嗯,对她来讲就是独一无二的体验。
杨玲:可能是这个情境造成的。
张沛超:如果碰上一个拿着锤子坐电梯的人……
王光:那一个片刻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永恒。
张沛超:他就希望给别人的生活中添加一点永恒。假如对方是个露阴癖……
王光:我也有遇到过,但是印象不太记得。
吴和鸣:没有什么创意,是吧?
王光:超无语……
张沛超:露阴癖有诊断标准没创意。
吴江:经验告诉我这有什么好看,但经验告诉我这不知道是什么,就会印象深刻。
王光:原来创意是这么来的,这叫独一无二,叫疯癫,叫颠覆。
李顺美:那做治疗时不需要经验?只要接受那个独一无二的感受?
张沛超:那我们这儿研讨干嘛呢?
王光:一起来。
吴和鸣:研讨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些从思想层面颠覆一下,技术层面好办。
吴江:思想要解放。
张沛超:谁有读古文字的?颠覆与疯癫的这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啊?
吴和鸣:树枝的尖端,山巅嘛,最高处、顶点。
王光:那个巅和这个癫不是一个字啊。
张沛超:不疯不癫何以成仙,就是一定要往最高处。
李顺美:高处不胜寒。
王光:那我们何以要发明自己的疯癫方式?
齐华勇:深层的需要?
……
王光:来看治疗过程。
张沛超:这一章够研讨一年的。
王光:先看这个治疗过程,我好想从来都没有完成过。
吴江:比如说刚才督导的那个案例,那个病人怕自己疯了,成为精神分裂。精神分裂对他来说的意味是不一样的。何以怕?精神分裂为何物?
吴和鸣:变成精神分裂有多少种可能?大家可以说一下。和病人讨论什么结果?
李顺美:没讨论,她说怕成为精神分裂。
吴和鸣:精神分裂之后呢,什么结果?
李顺美:她看到精神卫生中心楼上有住院的病人,她说“我怕成为疯子”。
吴和鸣:那就怎么样呢?
王光:失去控制了。别人看我就不一样了。
吴和鸣:还有呢?
吴飒:受到惩罚,被关起来。
吴和鸣:还有呢?
李顺美:没有爱了,别人都不爱她了,被抛弃。
吴和鸣:嗯,被抛弃。自己那么糟糕还浑然不觉。
吴和鸣:很有可能这个病人是不在我们刚才所说的情况之中的,我就是要强调这个。绝对不要以一个现成的假设去套某一个病人。
吴江:问题是,我们知道了这么多种可能性,然后病人有可能跟我们的这些可能性不一样。
吴和鸣:对,不是有可能不一样,而是就是不一样。
吴江: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可能性,然后我们不相信,会觉得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在这过程中必然有一个参考。才会有跟这个不一样的可能性。
吴和鸣:诗的语言,靠意象来表达,这个意象在每个人那里会不一样。诗人善于用这些语言来表达很多他难以言状的感受,我们在读的时候可能就接受到了一些。我们刚才说的那么多种可能A、B、C……都是一种语言,当我对A病人做的时候,好像发现A是他怕孤单,事实上在那个时候压根不是孤单,但跟孤单有点关系,但我们把它定义为孤单,但是它绝对不是A真正的感受。我们的那么多可能是试图在语言上把人的体验表达出来,但永远不能接近于那个真的东西。真的东西很多时候靠意象。……事实上,在治疗中很多时候都是有意象的,很多在自由联想的状态或者交流的时候就产生一些意象,能够去很好的表达。就是诗人啊。
吴江:换句话说我们还是要通过语言来达到这个状态。
吴和鸣:只是你要警惕,那个语言不是我们想的那个样子。
吴江:警惕,然后呢?怎么办?
吴和鸣:像诗人那样交流啊。
吴江:用什么交流?
张沛超:用一颗愿意听诗的心。
吴江:心是什么?
王光:花开的声音。
吴江:似乎来讲,那个东西无可依托。所以要警惕所有依托的东西都可能是障碍。
张沛超:在热带雨林中,有很多很高的乔木,看起来这些乔木把阳光都挡住了,但是就靠这样的荫蔽,藤萝类植物就上去了。这个语言的功能,即使遮蔽了一些但又揭示了一些。比如语言像一个球一样,抛来抛去,但在抛来抛去的过程中,每一侧的球跟以前不一样,是个不断往上走的过程,尽管以语言来交流但并不仅仅是语言。
吴江:有个比喻,语言是人类的家园。是否是剥离这个东西到那样一个状态,然后又要回到这个地方来。那个东西是什么样的,每个人都不清楚。
张沛超:海德格尔说的,语言是存在的家。但是只要有一个家,就必然有两种可能,一个是可以依靠,另一种是束缚。来访者达到一种什么样的自由呢?就是语言对于他来说,想回来就回来,想出去玩就去玩,但是它有个家。
吴江:去看看现存的个体诗人是什么状况?那个状态可以理解,但具体到我们个人的时候,情况是不太一样的。每一个诗人会有很多故事。
王光:表达方式也不一样。
吴江:看起来他是有问题,行为方式是不一样的,每个个人是不一样的。
王光:举一个治疗室中的例子,治疗室和来访者怎么作诗,做治疗?来访者说了一大堆,你听到了有个表达,比如,那是悲伤。用你的悲伤守着你的珍贵,这也是你听到的,张沛超说听了我很心疼。吴老师说你要替他去表达他心中的呐喊。哪一种方式是诗?都是?哪一种冲击最厉害?未表达的怎么表达?
黄帅:诗性的语言不是直接的表达,比如我是焦虑的、抑郁的、烦躁的。他会用一些意象去表达。以前说,治疗师帮他表达,说出来就意识化了,对他是有益的,那你现在又在颠覆,你是不是说孤独的那个A是不足以完全表达他的?
吴和鸣:所以你看诗经中的诗,什么结构?四个字四个字,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第四段,都是重复的,重复当中有什么?个别字眼稍微变化一下。就是这个意思。每一段都是也都不是。背个诗……
张沛超: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吴和鸣:我心伤悲,还有什么呢?
张沛超:我心疯癫,莫知我爽。
吴和鸣:你看关于我心就有很多种,同一首诗里面用的都不一样,就是因为主题对他来讲感受是非常丰富的。
李顺美:每一段只能表达一个部分,要不断地围绕这个主题,有更多的表达。
吴江:就是用感觉,语言表达到什么状态呢?就是一个空间。事实上,更多的时候它是一个时间,片段、状态,每一个时间是不一样的。如果表达一个空间,那么就是一个具体的,精神分析创造这样一个空间,但是分析的过程是一个时间的过程。
王光:但是在每一个片刻也是很具体的,只不过它是流动的。
吴江:是,每一个它都不一样,就有很多可能性。
张沛超:正是因为空间,才使时间成为可能。不管是客观时间,钟在走动,我们的主观时间,想起几年前、小时候,没有空间的话,时间就不可能对应我们的主体世界。但是来访者的内心,他的时间是破碎的,有的地方时空白的,有些是中断的,按老吴的说法就是倒带子,倒回去,在那一点上,本来已经拧得没有时间了,绽放出一朵空间的花来。所以那部分自体的连续感、时间感就有了。
吴江:比如说,以前我被狗咬了,然后经常回忆起被狗咬的场景,看上去内心有一个东西占据了空间,20岁想起被狗咬了和21岁想起被狗咬了是完全不一样的。当我到治疗室来的时候,我们无数遍去谈、去重复这些东西,它都是不一样的。但给我的印象,都是固定的一致的。
齐华勇:某些创伤,对病人而言是粪便,然后通过治疗师的一点点工作,以后可能是肥料,它自己可以有很多创造,是一朵花,一种肥料,是自由,释放了解放了。
王光:是,用粪便变成一朵花。
张沛超:它自己能结出果实来。
王光:是,但是好难啊。
张沛超:作诗容易,治病难。
王光:那可能质都变了。
吴和鸣:相反,应该说,变容易了,不是难了。谁不会写诗?
黄帅:感觉就是无论你怎样都有可能触碰到他。
吴和鸣:我们总在想,督导的时候,我是不是做错了、诊断不准确,假设不到位等等。事实上,完全没有必要。这不就轻松了吗?精神分析等于作诗。每次谈话就是在写诗。
黄模健:那怎么教精神分析呢?
吴和鸣:那就一起读诗经。
吴飒;是不是只有你的病人才能更好的学精神分析?
吴和鸣:开始写诗,成为一个治疗师。
黄帅:是不是在法国那边,并没有诊断的说法?
张沛超:法国人既讨厌DSM又讨厌ICD。
吴和鸣:不光是法国人,德国那些个治疗师就说,他们评估完了之后,随便写一个诊断。
张沛超:交给保险公司就好了。
吴和鸣:那交给保险公司不能随意。
张沛超:法国人连这个过程都省了。
黄帅:初学者还是要学这个诊断那个诊断。
张沛超:老吴的东西是在树尖的……
黄帅:我们还在树底下……
张沛超:所以你还得这样啊。
王光:我们在这边可以变成疯癫的人,对不对?我妹妹就说我,我看你们就是一群精神病,一群神经症给你们这群精神病治病。我们的这样一些思维模式到了外在的现实里,别人不一定这么看,我们觉得很自由,但是别人不是这样的。
吴和鸣:所以对你有看法。
王光:就是啊,我妹妹就你们就是一群精神病。
吴和鸣:她这话是个什么意思呢?
王光:疯癫啊。
张沛超:这是由衷的赞赏。
吴和鸣:是啊,她充满了羡慕。
王光:那是你的眼睛里看到了羡慕,她的眼睛里充满了鄙视。
张沛超:那是对羡慕的防御。
王光:她还讲到,我发现你做了这个行业之后,唯一的改变就是变得脸皮越来越厚。
吴和鸣:中国最大的财富是我们的诗词歌赋,登峰造极,唐诗宋词元曲,离骚、诗经,不得了。到了现在,不写诗了,但是大家都在唱卡拉OK。卡拉OK包括MP3,大家都在听什么?
黄帅:诗歌诗歌嘛。
吴和鸣:所以说,他们是直接的,我们是间接而已。
王光:这又是一个厚脸皮的表达。
张沛超:厚的很有道理。
王光:厚得其所。
吴江:所以病人就有空间嘛,更多可能性。
吴和鸣:他们是把歌直接作为诗,我们是把他们作为诗。境界就更不一样了。
王光:高的很。
张沛超:我们坐在树尖上,他们坐在二杈子上……
吴和鸣:小桥、流水、人家,你看这几个字就是非常丰富的……
大家:水墨画。
吴和鸣:病人在我们这里说的话,可以进入那种叙事的诗意的状态。病人的前一句话和后一句话完全不搭界,和诗歌一样,跳跃性。你可以把它连接起来。你的共情不就是在欣赏诗嘛?所以一回事。
齐华勇:我们在解释诗,做句读的事。
张沛超:任何人都能作诗,只要有懂诗的人。
吴江:我有一个病人,他说话我记录,回头一看,这不就是一首诗吗?
张沛超:读唐诗宋词跟那坐在治疗室中明显不一样。
吴江:那有可能是,你不要同我讲诗了,把握着问题解决了。怎么办呢?他说我很飘忽,来的路上是一个状态,来之后又是一个状态。不知道哪个状态时真实的,没法控制。
吴和鸣:那他写了诗的两段了。你把这诗读好读清楚,他就清清爽爽的出去了。
王光:问题是他们俩共同关注的东西还不同。他是爱诗的人,病人不是。病人关心的是另外一个。哦,我明白了……
齐华勇:诗内与诗外是断的,他自己也不懂。
王光:那是个象征。
吴江:看起来我们面对诗的时候有很多焦虑。
吴和鸣:对,不想当诗人吧,诗人没饭吃,是吧?诗人逍遥自在,多好。
王光:而且诗人的那种功能是可以帮你去修改那首诗的。我那个病人,我说治疗了这么多次,感觉我们的关系近了一点。他说,我觉得我跟你的关系还没那么近。
张沛超:这就是诗啊。
王光:是啊,在那一刻他帮你修改了。
吴江:所以精神分析治疗的宗旨就是把一个人变成熟人,正常人。因为诗背后是有焦虑的。
吴和鸣:如果要想的更彻底的一点,你要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活下去,必然要去当一个诗人。诗人不是离开现实的人。你看那个炸油条的人,每天都在写诗,他不写诗,这个油条炸不下来。他在幻想我今天来多少人,能卖出多少,明天我可以怎么样,沉浸在幻想的海洋里面,没有这个幻想支撑,他这个这个油条怎么炸下去?
吴江:他也会想,来不了这么多的人怎么办?
吴和鸣:是的,那就是一首忧伤的歌。
吴江:生活充满焦虑,所以我们必须有诗。
吴和鸣:对的。
王光:没有焦虑就做不出来诗?
吴和鸣:两个概念,诗刊上的诗那不是真正的诗,那叫呻吟,诗的一种。
齐华勇:那就是一切皆诗了?
吴和鸣:是,但你要去体会这个诗意。
齐华勇:更美的来享受这个世界。
吴和鸣:不是更美,也有忧伤痛苦的,从抽象的美来讲是美。如何享受?要正念。
张沛超:正念,如其所视。
王光:我那个病人,她现在帮家里卖茶叶蛋,每个提成5毛,昨天告诉我说今天卖了22个,挣了11块,这是诗的前半段,那后半段我怎么教她把诗做下去?难道要说能不能增加一点卖茶叶蛋的数量?这个不是诗啊。
吴和鸣:怎么不是诗呢?诗的第二段啊。
张沛超:强迫症是写这种诗的高手啊。
吴和鸣:你真的用诗意的方式去看待强迫症就容易理解了。
吴江:是,闻一多写了一个《洗衣歌》,洗了很多遍洗不掉这个世界的污浊。
吴和鸣:《十八摸》就是这样。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把一个人从头摸到脚。
王光:有这首歌吗?
张沛超:这首歌很正念的。
吴江:生活要狂欢嘛。


 正在提交中...
正在提交中...